文/红花会总舵
巴黎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造成了100多人的死亡,而臭名昭著的ISIS已宣布对此次系列恐怖袭击事件负责。有媒体将此次的恐怖袭击定性为法国版的“9·11”。这一剧变无疑已然构成了一次历史性的事件,必将对法国乃至世界的政治文化格局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一暴恐事件不由让人们再次回想起了美国学者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亨廷顿认为,在苏东剧变后,原有的、主导世界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冲突将走向淡化,而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将主导世界政治格局。这一预言提出于上世纪90年代,正值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从胜利走向胜利,另一名美国学者福山笔下的“历史的终结”似乎正在眼前,一个永久和平、民主、自由的千年福音社会似乎将在资本主义的最后胜利中向全人类走来。然而仅仅在2001年就爆发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后来的历史正如我们所见,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愈演愈烈,一直到刚刚发生的巴黎暴恐袭击,这场冲突尤未结束。历史似乎在不断地证实亨廷顿惊人的预见性。
然而,事实是否真如亨廷顿所预见的那样,仅仅是文明的冲突么?伊斯兰极端势力兴起的背后,仅仅是不同文明形态的根本性差异么?对这一矛盾的最后解决是否只能通过文明之间持久的战争,直至某一文明对另一文明的彻底征服?如果不是的话,那么这一冲突的本质又是什么?只有对这些问题做出清晰的梳理,我们才能够真正找到正确的解决道路。
一、外部的斗争还是内在的矛盾?
所谓“文明的冲突”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少见,中国古代汉族的农耕文明就曾和草原上的游牧文明爆发了持续时间长达数千年的斗争,中原王朝的主人几度易主为游牧民族的统治者。古希腊文明也曾和古波斯文明之间则发生过赫赫有名的波希战争,为我们留下了马拉松战役、斯巴达三百勇士等著名的传说。这一文明的冲突直到近代仍然构成人类历史的一条主线,例如西班牙对印第安文明的毁灭,西方文明对东亚文明的征服。这些文明的冲突往往伴随以血腥的屠杀和掠夺,乃至导致了某些文明彻底的毁灭(例如印度的原生文明、美洲的印第安文明)。
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冲突同样有着文明冲突的渊源。伊斯兰世界在历史上一度占领了北非、南欧乃至俄罗斯,而基督教世界则以八次十字军东征予以回敬。
然而,自近代以来,伴随着最后一次文明冲突的结束,覆盖全球的世界体系被建构起来了。这一最后一次文明冲突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全球殖民。不同于此前的文明冲突,这一文明冲突的特点在于,它打破了此前不同文明各自不同的经济基础,而在全球范围内重新确立了统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文明冲突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彻底胜利而告终,其他文明无一例外地走上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大特点在于,它必然是全球性的,必然要将自己的生产方式扩充到每一片可以触及的地区,也必然要实现全球资源、人口、资本的广泛流动。这就有史以来第一次通过经济联系的必然要求将全世界关联在了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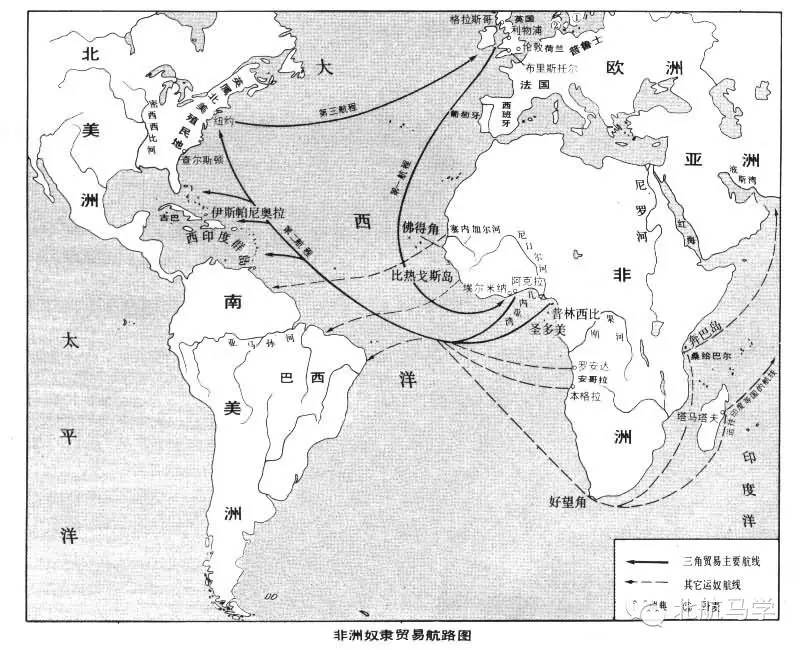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这样描述资本主义所开启的全球化进程: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今天的世界,已然成为了一个紧密关联的世界。任何穷乡僻壤的产出都将通过贸易售往全球,而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的吃穿住行,无不通过庞大的生产和贸易链条关联着整个世界。
在这一基础上,文明的冲突已然成为了一个虚幻的神话。试想,一个人能够真正反抗他的衣食住行真正来源么?对于流窜在沙漠里,宣称要反抗现代文明的恐怖组织来说,他们对于现代文明的依赖并不亚于生活在现代化大都市里的白领。他们的资金,石油美元,来自于西方和中国旺盛的能源需求。他们的宣传和招募手段,是现代化的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交媒体。他们的参与者,来自于全球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的穆斯林失意者。甚至被他们所图腾化崇拜的AK47,也是正在与他们血战正酣的俄罗斯人的发明。事实上,脱离开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和传播媒介,脱离开全球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他们所谓的反抗根本是不可能的。这一反抗手段与目标的截然对立,毋宁说是一场要提着头发将自己拽离地面的闹剧。
而这正与历史上一切的文明冲突有着本质性的不同。例如,在中国古代,汉族的农牧文明同草原的游牧文明之间,有着截然不同的经济基础,除了少量的货品交换,二者之间并没有对彼此的经济依赖。同样,历史上十字军和哈里发之间的对立也是如此,哈里发的统治和军队并不依赖于西欧农民的生产。这样的冲突实质上乃是一种外部性的冲突,冲突的双方对于彼此都是外在的敌人,其典型的冲突方式便是争夺土地和人口的大规模战争。而在伊斯兰恐怖主义组织这里,我们看到的主要斗争方式,是通过潜入内部的自杀式袭击,制造恐慌等等。这一斗争方式的前提在于,反抗者本身正是对方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暴恐分子本身就是袭击国的公民,惟其如此,恐怖袭击才具备可能。
这一从内部进攻的反抗方式、对西方文明的技术手段和资金的严重依赖,已足以证明这绝非是什么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一场现代文明内部的叛乱。
二、宗教旗帜下的绝望反抗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卡尔·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作为恐怖主义头目的所谓“哈里发”和其他领袖自然有他们神学的目的,其背后的金主也有着各自的政治诉求。但最为根本性的问题在于,它们的基层参与人员从何而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青年人不图名不图利,义无反顾地加入到这场注定没有前途的事业中去呢?或者,套用马克思的比喻,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青年走向精神的鸦片呢?
事实上,就马克思的这个著名比喻而言,我们过去一直存在着误解。在马克思时代的欧洲,鸦片并非完全意义的毒品,更多地是作为一种镇痛剂来使用,类似于今天医院为晚期癌症患者注射杜冷丁和吗啡。其并无实际的治疗效果,但却能有效缓解病人的疼痛。在马克思看来,宗教的意义正是如此,正因为有了在实际生活中无法解决的痛苦,人民才走向宗教的精神慰藉。
对于ISIS所吸纳的穆斯林群体同样如此。在穆斯林世界中,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于,原教旨主义运动并没有得到通常更为保守的年长者和农民的广泛支持,其社会基础反而更多地在于本应更加开放的城市里的青年人。而这一现象充分地表明,保守主义的复兴绝非单纯的意识形态因素,而是有着更为根本的现实基础。这一现实基础事实上就表现为发展的不均衡,特别是2008年以来进一步加剧的经济危机。
据报道,在阿拉伯国家,28%的城市居民生活在市郊的“贫民窟”,不足3亿人口的阿拉伯世界贫困人口却接近9000万,至少73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中国人心目中富的流油的沙特,尽管石油美元让皇室拥有高达180亿美元的巨额财富,但据《卫报》的报道,有多达四分之一的沙特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沙特学者罗西说:“国家把穷人隐藏得非常好。精英看不到穷人的痛苦。人们很饿。”而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青年人的就业情况尤为堪忧。根据2013年的一项报道,阿拉伯世界的年轻人失业率全球最高,平均高达25%,部分国家达到50%。
不需要任何的理论,仅仅从日常生活经验出发,我们便可以想见,当四分之一的青年人找不到工作时,会是怎样的一个社会状况。埃及政治评论家穆罕默德·海卡雨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最贫穷的地区蓬勃发展并从贫困中得到滋养并不是偶然。如果你是一名年轻的阿拉伯人,如果你受了教育,又回到了你的村庄,但是找不到工作,你自然有可能变成激进分子。在过去,你可能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而如今你会变成为一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
当无所事事的青年找不到任何个人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前景时,自然也就感受不到社会与自身的紧密联系,也自然会从绝望中产生愤懑,走向反抗。这一点,在任何国家、任何群体中都并无不同。而伊斯兰教作为早已潜入他们生活血肉之中的文化传统,自然也就成了他们寻求精神慰藉和抗争武器的第一选择。对现实的不满导向了对传统的推崇。在极端宗教主义这里,这些失业的边缘青年不再是世俗社会里的loser,而成为了为真主所看重的圣战者。黑格尔说,人有相互斗争谋求承认的需要。这些在市场的竞争中被打败,得不到任何承认的青年,转身通过拿去古兰经和AK47谋求另一种形式的承认。宗教极端主义成了阿拉伯世界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一碗心灵鸡汤,为处在社会边缘的失业青年们提供了生活的意义。
其实,同阿拉伯世界一样,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失业青年同样也会走向各种形式反抗的道路。希腊的青年失业率高达60%,其结果就是走向从无政府主义到法西斯主义的各式街头运动。而在阿拉伯青年这里,伊斯兰教的特殊性使其成为了相较其他反抗形式更为优先的选择。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公共号推送转发的另一篇文章《作为一种操作系统的伊斯兰》。而在历史上,当共产主义运动构成反抗资本主义体系的大潮时,穆斯林青年也曾豪不介意地搭上了共运的列车,高举其“阿拉伯社会主义”的旗帜。只不过此一时、彼一时,当共产主义运动走向衰败之后,留给阿拉伯愤怒青年的就只剩下先知的训斥了。
三 、出路何在
“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宗教是它的神圣光环——的批判的胚芽。 ”——卡尔·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在伊斯兰极端宗教势力的威胁下,西方社会普遍的反应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右派为代表的排斥和反击,典型地如法国的国民阵线主张禁止移民、禁止向穆斯林学生提供清真餐等等;另一种则是左派继续强调宗教自由、族群平等的政治正确,呼吁伊斯兰内部的世俗化改革。
然而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的道路事实上都是无法根本解决问题的。如果按照右派的思路,事实上是要将占法国人口的10%的穆斯林彻底推向敌对面,这必然导致更为严重的族群分裂。而对于左派所呼吁的世俗化改革而言,则彻底忽视了伊斯兰极端主义产生的现实根基,一厢情愿地指望在经济上绝望的穆斯林走向更加温和的信仰。事实上,这两种解决思路都在根子上将问题简化为了文明形态的冲突,只不过左派认为这一文明冲突能够在西方文明多元化的政治框架下得到化解。
然而,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于宗教信仰或文明形态的冲突,而在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身的内在矛盾。越是试图在文明形态或宗教信仰上做文章,则越会导致宗教或文明认同裂痕的加剧,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不论是宗教还是文明,其本质都是一种对共同体的意识形态认同,通过对特定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同一化来为维系特定的共同体。而之所以选择加入这一共同体,除了传统的影响之外,最为根本和直接的因素就在于其能够部分(哪怕是虚假地)满足我的需要。而要摧毁这种虚假的满足,就必须提供真实的满足。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要实现人民的现世幸福。
既然现有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乃是宗教极端主义的温床,那么要想彻底消灭宗教极端主义,就必然只能走向对这一经济政治秩序的彻底变革。既然宗教极端主义为穆斯林青年所提供的不过是一种虚假的满足,那么就要为他们提供一种更为彻底的、唯物主义的解决方案。任何的调和都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