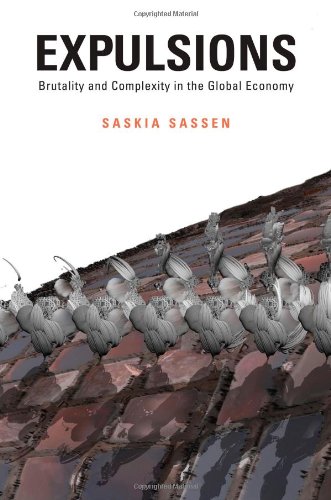澎湃新闻记者:沈河西
贫穷和分配不公这类熟悉的概念已经无法帮助我们理解今天的现实,我们需要发明新的语言——这个世界经济的运行逻辑是驱离,让人无家可归,让生态圈遭到毁灭。中产阶层可以一夜间沦为新贫,每个人都可能被逐出社会生态圈之外。这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莎士奇亚·萨森在《大驱离》一书中向我们揭示的全球经济的残酷真相。
萨森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全球思想联合委员会主席,她的著述聚焦在全球城市、全球化、全球资本主义、当代城市社会运动等议题。在如今汗牛充栋大批判当前资本主义的著述面前,《大驱离》带给我们怎样新的思考?我们究竟面料怎样的被驱离的境地?面对这样的境遇,我们如何寻找行动的主体?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和萨森教授进行了对话。
熟悉的语言已经无法捕捉更大的现实,我们需要发明新的语言
您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我们需要新的语言,因为当我们讨论不平等、贫穷、监禁、剥夺家园等社会不公时,单单用熟悉的语言已经无法捕捉更大的现实了,这是您写作这本书的初衷吗?
萨森:是的!我想要直面正在浮现的这些状况。对于这些状况,我们缺乏一张地图,而我想要理解它们可以多广地延伸到社会生活,穷人可以变得多穷,被毒化的土地如何变成死土等等。我的论点是那些熟悉的状况可以呈现出多么极端的面貌,极端到常规的范畴已经无力再捕捉。比如,你不仅仅是贫穷,你无家可归,饥渴交迫。或者,说到土地和水,不仅仅是土壤和水质退化,而是变成了死土和死水,完了。我们往往停在那个极端的点上,但没有走进去。这种极端太巨大,太丑陋了。我们缺少概念去捕捉这样的极端。
我把这种极端的状况命名为“驱离”。凯恩斯主义时期也存在驱离的状况,但今天的驱离逻辑较那时来得更广泛,更极端。这种驱离起始于1980年代,那时西方的福利国家以及一些拉美国家的福利制度不是被摧毁就是面临巨大压力。从某种程度上,以人为导向的福利制度也是某些共产主义国家的特征,在这些国家,福利制度也开始瓦解了。
在这本书里,你用了一种不太理论化的分析框架来理解今天的状况,这构成了您和现有的批判性的、充斥理论术语的著作的显著区别,您的写作似乎更接地气,为什么选择这样一种分析方法?是因为有预设读者吗?
萨森:我的问题和出发点是:在哪一点上,我们需要和主导性的理论化保持距离。我们通过理论来理解,理论使我们不至于成为细节、经验数据的囚徒。我的下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有必要去理论化,回到地平线,以这样的方式重新理论化。
另一个解释是,对于有的问题,我们需要去掉那些更宏大的框架,然后看清楚某个问题发生的状况和过程。
举一个例子,我在书中把俄罗斯北部生产镍的城市诺里尔斯克和美国的金矿城市蒙大拿进行对比,这两个地方都遭到巨大的毁灭。两个城市各有其历史脉络:一个是共产主义的,一个是资本主义的。我问哪个对尽头的世界更重要:共产主义历史的那个还是资本主义历史的那个?还是说它们的环境都遭到了巨大的毁灭。在早先的阶段,重要的是因为冷战造成的各自不同的历史地理状况。但在今天的这个世界,两个城市都具备足以毁灭环境的能力。通过这样的方式,我质疑了过去的那些范畴。
金融卖的是它没有的东西,它什么都不生产
这部书的副标题是“全球经济的残酷与复杂”,您在书中也提到“简单的残酷”这样的概念,怎样理解复杂和简单的辩证法?
萨森:这本书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去揭示复杂的知识如何生产驱离。这也就揭示了,我们所仰之弥高的那些复杂知识其实就位于一个长的交易链的起点,它最终会造成非常简单的驱离。我选择都是非常极端的例子,因为这样可以使那些模糊的东西变得可见。在知识生产的层面,我尊重专业化的知识,它们对于研究、发现有很重要的作用。但当我们把这些知识系统放到一个更大的交易链条里时,我们就会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复杂的知识如何造成简单的驱离后果?比如,在金融化那一章里,我说如果你想要理解金融,千万别问金融家,因为他会抛给你一套非常复杂的语言,你一个字都听不懂。跟传统的银行不同,金融不是关于钱的。传统银行卖的是它有的:钱。金融卖的是它所没有的东西,这就是它的创造性:它发明工具。最终,金融只是一整套工具,它什么都不生产。金融公司要想营利的话,它得投机在别的产业的产品上。它们把一切都金融化:二手车、学生贷款、次贷等等。当你意识到这点时,你就会看到金融资本主义的危害。你会发现它用一套非常复杂的知识来进行初级的林润榨取。我们当前的经济雇佣的是卓越的头脑,对这些人来说,这一切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他们只关心它的运作是否顺畅,但他们不去看看这会给别的产业部门造成怎样的后果。
从另一方面来说,正因为很多问题被人为地复杂化,我们更需要将它简单化。你不能指望用某个产业、领域的所谓专业人士的语言来理解问题,你要问:你们到底在干什么?比如说到液压破碎法,你知道这是用来干嘛的吗?它是用来毁灭土地的!
在书中,您提到当前的驱离机制始于1980年代初,但您似乎避免用“新自由主义”这种在学术界和媒体报道中常用的词汇,为什么?
萨森:没错,是这样的。在有的情境里,当我在和不那么知识化的受众对话时,这是一个比较有用的词汇。但这个词只能涵盖一部分我想说的意思,它跟正式的政治体制相关,而这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它并没有处理金融如何重塑经济,各类复杂的知识如何制造残酷,这些特点是我感兴趣的。“新自由主义”这样的词太局限性了,它主要属于某个特定的时期或特定的地理区域,如西方、全球北方等。
在这本书里,你讲到战后的凯恩主义是吸纳式的,即诉求是把尽可能多的人纳入到这个系统里,发展到80年代后就变成了相反的以驱离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给人的感觉是您依靠的是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二元对立的框架。然而,这两个阶段是不是也有一些连续性?譬如说,这种驱离的逻辑会不会在凯恩斯主义阶段就可以找到源头?
萨森:大多数读者对凯恩斯主义阶段这个说法比较熟悉,用这样一个说法可以便于我为分析当前的阶段给出一个参照。当前的阶段的特征不是扩大大众消费,而是扩大榨取的逻辑,这个榨取的逻辑造成了大量的驱离而不是吸纳。
那凯恩斯主义阶段和当前的阶段的共同点就是都是资本主义,企业资本主义。但是它的运作逻辑的形式从1980年代起发生了变化,对于企业来说,全球化意味着私有化、去管制化。
在书中,你揭露了一个惊人的现实:监狱的私有化,以及将没有工作的人关押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对于这些行为,有反对的声音吗?
萨森:长久起来,就有人一直在和这种虐待犯人的监狱作斗争,反对监狱的私有化。但对社会大部分公众来说,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有多么极端。比如,在美国,情况最极端,但大众只是把它当成一桩生意,而不是一种压榨人的机制。
在书中,您提到政府对于下层人群的脱贫、医疗等投资不足最终会危害社会上层,您能否再详细说说为什么?
萨森:我想到的是极端的状况。如果你让都市里的穷人染上传染病,他们可能会把这些疾病带到办公室、家里、学校里。传染病会在穷人社区发展壮大,但会进入到城市里,比如进入公共交通场所。
近来,西欧的难民危机引发全世界的关注,但是您在书中指出接收全世界大部分难民的其实是不发达国家。但在主流媒体的报道中,发展中国家的难民问题得到的关注远不如西欧,为什么呢?
萨森:在西方历史上,移民是非常熟悉的形象: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他们会在西方定居下来,开始做点小生意,把钱寄回母国,想象有一天可以回归家园。而难民则是完全不同的一类人——他们是更大力量的牺牲品、被驱赶的魂灵、没有政府支持的人。
今天,有一个新的类型的移民:他们的中心是地中海、安达曼海和中美洲。在我看来,原因并不是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迁徙背后的推动力是祖国内部的冲突、战争、土地剥夺、生态的破坏(因为土地和水被毒化、干旱、盐碱化)、矿难等等。他们的整个家园和社区都从故乡连根拔起,故土上已经没有家园可以回归了,家园变成了战区、荒漠、被淹没的平原、私人的城市。他们无家可归。
在书中,您用了很多例子来描述驱离如何成为当前全球经济的运行逻辑,但是否“纳入”和“驱离”是并存的,可以共同作用?比如,今天主流的性少数运动一方面打着“同化”的旗号,一方面又在排斥底层的性少数群体?
是的,完全正确。我确实认为注意的是,提供一个表达诉求的空间是很多人所关心的。尽管经济越来越受控于少数的有权势的人,越来越多的的政府机构其实也在支持经济权力的集中,尤其是美国和英国的中央银行。这些运动并不会触及到经济权力的集中,而可能是某种障眼法。当然,这些运动发生本身是好事,但它们也在掩盖权力、财富集中的事实,掩盖中产阶层越来越贫困的现实。
街头是一个不确定的空间,没有权力的人可以变成创造者
在一篇文章讲到中产阶级运动的文章里,您说这些运动反抗运动更多的是针对政府而不是“资本主义”或跨国资本,为什么?
萨森:好问题。二战后的自由民主国家所发展的这些项目的受益人主要是中产阶层。当自由民主国家变成新自由主义国家之后,随着这些项目的缩减和私有化,中产阶级首当其冲,最先感受到好日子过去了。穷人从来也没得到过太多政府的好处,而富人总归有自己的财富,没有必要依靠这些政府项目。所以,这些变化伤害到了中产阶层的利益,他们的矛头自然而然也就对准了政府。
在书中,您写到说,历史上,受迫者起来反抗主人。今天,尽管世界各地反抗运动不断,但这样的反抗总是很难成功,因为受压迫者已经被驱离,他们只能在距离压迫者很远的地方生存,能否再详细谈谈这一点?如果这样的话,反抗如何可能?
萨森:如果你回顾历史趋势的话,没有一个权力体制是可以万世长存的。权力可以部分地摧毁自己,然后为那些正在团结起来的人提供空间。此外,我认为在城市里,无力者可以和权力有常规的互动,这很重要。城市里,权力也无法永远维持。我认为,城市有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特质,比如它的人群,它可以成为一个没有权力的人的空间,让那些没有权力的人获得能动性,因为这不是一个完全被控制的空间。
我在有的地方写到过我对近些年对占领运动或“街头政治”的分析。广场是一个仪式化的公共空间,你要遵循一套特定的规范。而街道则是一个不明确的公共空间,你甚至不会把它看成一个公共空间。当我说街道的时候,我不是仅仅指一条街,它可以是一片空地,因为一栋房子被摧毁了。占领运动包括在被废弃的大楼前静坐,或在公共空间里集聚。通过这样的方式,没有的权力的人可以制造领土,创造历史。
你有一种自然的冲动想去占领。当你造了一个大商场,把街坊邻居的街区推倒了,你把一切都私有化了,你就失去了那种街道的不确定性。可能你要造的这个建筑非常复杂精美,但是你减少了城市空间的复杂性、多样性。
中国中产无法壮大,因为他们赶上了财富积聚集中于上层的新自由主义时期
在书中,您指出驱离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而不是某个国家或地区所特有的。那当我们说到中国时,经常听到诸如“中国例外论”这样的说法,您认为中国例外吗?您有没有注意到在中国也存在您说的驱离的现象?
萨森: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富裕,它当然也在生产巨大的不平等。尽管中国为穷人提供的公共服务要比美国来得多得多,但中国贫困的工人阶级也已经开始浮现,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当然部分大城市也出现这样的贫困阶层,而富人越来越富。所以在今天的世界,一个更深的经济逻辑在进入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许多穷国,你会发现富人精英基层,而穷人则比20年前更穷。
在书中,您提到尽管全球金融化对人民和生态系统造成巨大破坏,中国的金融资本却帮助老百姓摆脱贫穷,您能再详细说说吗?您是否认为中国提供了一条替代性的解决方案?
萨森: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中国为大部分人口建造了基础设施、住房、医院、学校。现在你们出现了不同的阶段:极度富裕的精英,非常富裕的上层中产阶层,一般的中产阶层,以及有一部分人已经失势。对最后这一部分人来说,城市变得越来越昂贵,因为它们是为富人服务的。
当我们在不同的语境和地区用“中产阶层”这个词时,比如说美国的中产阶层、欧洲的中产阶层或中国的中产阶层,这个“中产阶层”是同一个意思吗?还是说是有区别的。
萨森:即使在一个国家内部,中产阶层也是有显著差异的,更何况不同的国家。在西方,中产阶层有这样一些特点:他们不是工厂工人,他们子孙的境遇比父辈好很多,这种好境遇到了1990年代走到了头;他们获得很多政府服务,在一个特定的城市或社会里,他们是同一群人。
在中国,一个让人担忧的现实是中产阶层没能壮大,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萨森:就我观察到的来看,一个有点出乎意料的趋势正在发生:中国经济和社会所发生的诸多变化正在造成这样一个趋势,即中国的阶级问题也跟美国、拉美等地区合流了。基本上,今天的经济体系造福于20%的上层人士,这部分人较传统的中产阶层富裕得多,而过去的中产阶层则正在变穷,或者不像过去的20年里那样财富上涨。在美国、拉美、欧洲以及一些较繁荣的非洲和亚洲国家都出现了这样的现象,现在中国也发生了这样的状况。对于中国的中产阶层来说,他们受惠于改革开放,那时西方的制造业转移到中国,这帮助催生了中产阶层,但同时不幸的事,他们变富的这个阶段又赶上了新自由主义转向造成的财富积聚向上层集中的阶段,因此无法壮大。
在中国,一个有点矛盾的现象是中国的中产阶层在文化趣味上的层面上是资产阶级的,但是在社会地位、财富等方面却跟真正的有产者有巨大差距。因此,您认为当我们在分析今天的中国时,中产阶层这个概念依然有效吗?
萨森:这个点有意思。这是占人口20%的上层的中产阶层,不是1%或2%或5%的那一部分人,而是这下面的很大一部分人。这个阶层比过去传统的中产阶层更富有,在教育和文化方面也更不同。
近些年,许多中国城市都出现了“邻避运动”,这些运动和西方有什么区别?您怎么看待这些运动?
萨森:就像最开始的两个问题里提到的,中产阶层正在发生进化,出现了一种新的中产阶层,即上层中产阶层。在邻避运动的例子里,也有许多更一般的失势的中产阶层,他们切身感受到受到了更贫穷的工人阶级邻居的威胁。
在一些大城市如上海,有的人为了反思或反抗都市空间的缙绅化、私有化,他们尝试着复兴都市文化。比如有人学60年代法国思想家居伊 德波进行城市漫游,您觉得这些尝试在政治上真的有效吗?还是说只是一种小资的文化趣味?
萨森:这也得看情况。有的文化尝试是可以很激进的。腔调玩乐、幻想等也不一定就是小资色彩的,它也可以是很激进的。在一个城市里有一些激进的文化因素是重要的,即便并一定就要通向革命。它们可以为年轻人提供一个文化空间,使他们发展自己的政治文化上的批判观念。
举报
© 本文版权归作者 沈河西 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