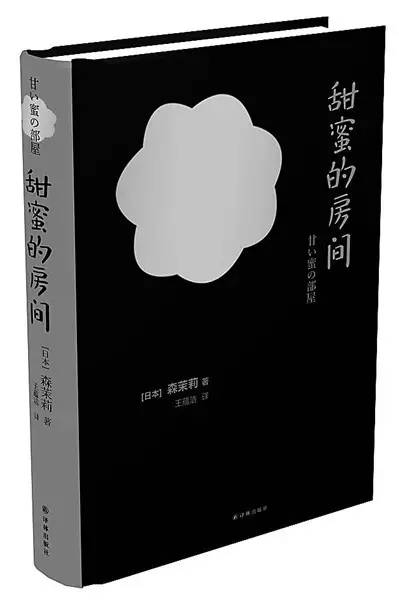编者按: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耽美”文学在网络上渐成蔚为大观之势,影视剧里公然卖腐以讨好大众的做法近年来也数见不鲜。最近几年的热播剧都有意无意地求助于腐文化来博得眼球,从《神探夏洛克》到《红色》,从《琅琊榜》到《伪装者》,腐文化从最初颇具先锋性的姿态,渐渐沦为一种噱头,一种无处不在的装点,甚至成为屏幕上“新的保守主义”。与大众文化里不断被人谈论的“腐”相比,腐文化的文学载体耽美小说在评论中却处于相对冷落的地位。今年上半年,被称为耽美界“祖师奶奶”的日本作家森茉莉的作品《我的美的世界》和《甜蜜的房间》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大陆正式出版,以此为契机,当代文化研究网推送两篇与耽美有关的文章。张冰的《论“耽美”小说的几个主题》发表于2012年,论文从森茉莉描写的“甜蜜的房间”谈起,梳理了这一文类的发展历史,并清理了与之相关的几个概念。论文重点分析了“耽美”小说当中的几个重要主题,如“耽美”中的独特感觉、“少年爱”的内涵、“虐”的情感表现、颓废的艺术风格和精神体验等,借此讨论“耽美”的造梦机制,它在流播过程中的变异以及它的内在困境。和论文写作时的状况相比,如今的“腐”早已成为一种事实进入到流行文化当中,无论是试图理解还是大加批判,它已强韧地植入了年轻人的文化想象。看上去,人们似乎喜欢将“腐”挂在嘴边,但在这个不断泛化的过程里,“耽美”逐渐丧失了文学艺术上的生产性,呈现出一种疲软的态势。本文提供了进入这个问题的几个视角,期待以此打开较为严肃的讨论空间。本文发表于《文学评论》2012年第5期。
作者简介:张冰,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任教于浙江外国语学院中文系。
转载自当代文化研究网
(胡歌和霍建华为某时尚杂志拍摄的照片,网友称CP感爆表)
“耽美”作为一种亚文化现象,在中国大陆最早出现于1990年代初。当时,一些有着“耽美”风格的动漫作品由日本传入中国,吸引了一批青少年读者,特别是年轻女性。这批最早的“耽美”爱好者大多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和其他沿海发达地区。到了90年代中后期,随着网络的普及,中国大陆出现了一些涉及“耽美”内容的网站,迷恋“耽美”的女孩们于是获得了在网络上交流和联合的机会,形成了所谓的“同人女”【1】群体。2000年后,随着网络文学的流行以及商业性文学网站的出现,“耽美”的影响面日益扩大,许多大型文学网站如晋江、连城等,都先后开辟“耽美”专栏,专门的“耽美”小说网也应运而生。【2】这一时期,网友的原创作品数量剧增,水平参差不齐,“同人女”的年龄也呈低龄化趋势。“耽美”不仅成为最重要的网络文类之一,还和玄幻、武侠、历史、穿越等文类彼此混杂,以“跨界”的方式扩大着自己的“势力范围”。一开始,至少在名义上,包括“耽美”和其他“同人志”【3】在内的小圈子创作坚决反对商业上的牟利,但随着“同人女”越来越多,“耽美”也变成了商家眼里有利可图的东西。专门的“耽美”杂志和书籍通过正规或非正规的渠道出版发行,获得了广泛的流播。
时至今日,“耽美”小说的题材、内容、风格都极为庞杂,但仍然保持着一些基本特征。“耽美”(日语发音TANBI)的日文原意是“唯美、浪漫”,体现在文学中,就是致力于表现“能让人触动的、最无瑕的美”【4】。基于这一旨趣,“耽美”小说热衷于雕琢辞藻,追求文字的繁复华丽。“耽美”本来并无特定的表现内容,但现在人们谈及它,一般是指“bl”(boy’s love)作品。顾名思义,“耽美bl”的核心主题在于书写俊美男性之间的爱情,在角色设置上有明显的“攻/受”【5】之分。
“耽美”通常被放置在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位置。“耽美”是20世纪日本文学中“唯美主义”的对应词,和经典唯美主义文学一样,“耽美”描写情欲和死亡,着力于表现感官享乐和极致的感性之美。这些主题在常人眼里有时或显病态,但在其发生上却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在欧洲,唯美—颓废主义是“近代文明和近代人文理想发生根本危机的第一批精神产儿”【6】。19世纪的颓废艺术家把外部世界看做是一个衰朽的过程,人生乃至整个文明都在无意义的自我耗竭中走向末路,而所谓“唯美”,则是“自觉到颓废的人生宿命之后转而对颓废人生采取的苦中作乐的享乐主义立场”【7】。作为唯美主义在当代大众文化里的一个变种,“耽美”小说也浸染上了世纪末的颓废情调,“同人女”宣称:“不要把乐趣变成负担,不要担心明天,下一小时的去向不在我们掌握之中。与其苦苦地思索,不如快快乐乐地享受。”【8】“同人女”强调男性之间的恋爱“不涉及繁殖”,既为了保证恋情的非功利性,也从生理上斩断了人类和未来相延续的关联。不过,“耽美”毕竟是一种为大量普通少女所喜爱的文学,难免成为写作者心目中理想恋情的投射,因而“耽美”又总是带有青春期浪漫、纯情的色彩。
一个颇有传奇意味的细节喻示着“耽美”和日本唯美主义文学的亲缘:被“同人女”视为“耽美”小说鼻祖的森茉莉还具有另一个身份——日本唯美作家森鸥外的女儿。森茉莉的作品通常以一老一少两个男子相恋为基本的故事情节,这一叙事模式也为后来的“耽美”小说所广泛沿用。同为“耽美”作家的栗本薰认为,这种一老一少的男子之恋实际上是父女之恋的置换。【9】森茉莉十六岁远嫁巴黎,告别了在父亲膝下的日子。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之后,有整整十年,她躲在积满灰尘、蟑螂横行的公寓里写作。对于此时已年过五十的女作家来说,写作可以令她尽情地沉湎于逝去的时光。那些记忆中精致的小物件连同父亲无节制的宠溺,在她笔下似乎永远蒙着一层少女般鲜艳的光泽。在自传性小说《甜蜜的房间》【10】里,早慧的女主人公藻罗从六岁起便在心中建造了一道由毛玻璃构成的墙,它有效地放大了她的内心,却隔断了她和外部世界之间的真实交汇。这个极富想象力的女孩还幻想着在自己的周围筑起另一个极度透明的玻璃房间,从那儿望出去,外部世界会变得比真实存在更加美丽,更接近自己的理想。在某种意义上,“耽美”作品就如同森茉莉笔下的这道玻璃墙壁,外在世界通过折射映现在玻璃之上,发生了变形。玻璃墙上漂浮、游动的形象,是孤独中的安慰,让人领受梦境般的沉酣。作为外部世界的碎片,它们清浅透明,似乎并无深意,然而我们不妨把它们看作一枚枚有待拆解的符号,通过解读这些符号,我们也许能够弄清楚那一层玻璃的质地和光学机制。
一
“耽美”的兴起和城市独生子女一代的生存状态密切相关。1990年代以后,“宅”【11】在中国逐渐成为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们依靠一根网线,足不出户就能呼朋引伴。“同人女”便是这样一群“宅”在电脑前的人。在一个学业和工作都分外枯燥的人生阶段,“耽美”成了她们克服孤独感的重要媒介,又“腐”又“宅”的女孩往往自己并不热衷于恋爱,却爱看虚构中两个美少年的恋爱。外人很难理解那种激情:废寝忘食地阅读自己喜爱的作者的全部小说,每天等在电脑前追着最新连载,和同好彻夜长谈……“耽美”带给“同人女”无穷的乐趣和感动,“实在比恋爱还开心”。调查显示,有4成的“同人女”认为在网络上的活动是她们交友的重要来源。和现实世界不同,网络世界另有一套礼仪规则,因此,一个在现实中有自闭倾向的参与者完全可以在网上如鱼得水,和人沟通无碍。【12】相比于公共空间的萎缩和现实中人际关系的枯竭,“耽美”小说自身反而构成了一个自足的空间,足以令人暂时忘掉那个压抑、暗淡的真实世界。
唯美文学为孤独的主体开出的解救之途是依靠人的“感觉”和万事万物建立起一种特别的联系。1910年,日本作家上田敏在自传性小说《旋涡》里,曾勾画过这种状态:“在宇宙的广漠和威力面前,心灵的寂寞和软弱是人生最大的悲哀。……如果能从过去贪吃的下巴上恢复几分生活的感觉的话,即使不那么完全,不那么纯粹,终究也可以聊以自慰了。……不堪寂寞,为忘却而悲哀的人类,哪怕能从这里找到一点自己与万物的联系,证明自己与同类的类似、交往和共存的事实,则也可得到一点慰藉了。”【13】那么,“耽美”当中的独特“感觉”,到底是怎样的呢?
最直观的层面上,对“美人”(“耽美”对美男子的称呼)的欣赏所获得的视觉快感,构成了“同人女”彼此分享的重要内容。美丽是最重要的东西,而“只要说它美丽,那么别的一切说法都无关紧要了”【14】。“耽美”的主角常常是风华绝代的美男子,他们身上集中了男性和女性的双重特征:既有男性的英俊也有女性的柔美,既摒弃了男性的粗糙线条又避免了女性的优柔粘滞,简直是人类的躯体在有限的想象中可以达到的极致。这种超越了性别的美在外人看来或者有失于矫揉造作,但对“同人女”具有致命的吸引力。“同人女”把“耽美”小说打造成一种极为视觉化的文本,“观看”在这一阅读活动中占据着关键位置。小说不但为读者提供了栩栩如生的形象,也提供了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同人女”在“耽美”里看“色”,也看“情”。天长日久,她们习惯了“意淫”(网络上的拼音缩写为“YY”),乐意把她们所看到的“耽美”小说以外的美男子也“撮合”在一起。“意淫”一词本出自《红楼梦》,这个略显生僻的词如今却在网络上风靡,实在耐人寻味。李欧梵在论述《红楼梦》与唯美—颓废的关系时,对“意淫”做了如下的解释:“把女子作为追求的对象,把这个追求过程表现在俗世生活中,就是尘世的爱和欲,但用美学的眼光来看,却是一种‘意淫’——一种对色和情的极致追求,……在《红楼梦》中的‘色’是一种辉煌的美,这种美需要‘情’的极致而使之表现得灿烂无比,所以‘色情’才是‘淫’的表现,都是惟美的……”【15】当然,在“耽美”里,进行意淫的主体和被意淫的对象之间的性别发生了颠倒。
在一部以电影明星和摄影师为主角的“耽美”小说《浮光》【16】里,作者着力开掘了几组影像与生活中“看”与“被看”的关系。由于选取题材的特殊性,“观看”这一“同人女”最钟爱的行为被小说叙事放大、放缓了。无论是故事里人物对演员的凝视,还是文本内部电影中演员间的相互凝视,抑或是文本外“同人女”对小说人物的凝视,在这三重观看当中,男性都替代了女性,成为被观看的对象。而“耽美”里女性眼光的出现,并非是对于过去男女二元权力关系的简单反转。主角言采【17】是一个魅力十足的电影明星,兼具阴柔与硬朗气质的他比小说里的女演员更有资格成为镜头眷顾的宠儿。每当摄影机的特写镜头停留在他的脸上,或者舞台上的追光打在他身上时,他整个人就会焕发出夺目的光彩。就像小说里的女孩潘霏霏说的:“只要看着他银幕上的面孔,总能轻易地坠入一厢情愿的爱河之中”。潘霏霏热衷于追逐偶像,不放过任何一个和言采接近的机会,是娱乐时代的典型“粉丝”(fans)。有趣的是,小说中另外一个言采的爱慕者,男模特卫可,却持有一套和“粉丝”完全不同的追星理论。他清楚地知道他看到的言采只是幻影,但他乐于保持这种有距离的美感。这番自我表述听上去同样适用于“同人女”。“同人女”对于“美人”的凝视所获得的视觉快感,并非以占有为目的。她们自觉地和观看对象保持着一定距离,丝毫不想去介入对方的生活。在《浮光》的“番外”【18】里,老去的卫可已结婚生子,他虽然爱慕着言采,却始终不曾把言采当做现实的欲望对象。这也像极了多数“同人女”的现实状态:生活中保持异性恋的性取向,在幻想里通过对美男子的凝视获得满足。爱慕对象是永远不可获得的,但“同人女”却可以在阅读中获取一种更高级的愉悦之感,一种牺牲自我、成全他人的快乐。《浮光》里,跨过了银幕上的明星和银幕下的普通人之间的距离,最终“得到”“活生生的”言采的,是年轻的摄影师谢明朗。按照“bl”小说里的“攻/受”关系来说,谢明朗是“受”的一方,这个人物的个性形象和身体体验与女性极为接近,如年龄上比言采年轻,社会地位相对较低,性格害羞、内向、被动等等。或者可以说,虽然“同人女”由于性别身份没有直接进入到作品当中,但谢明朗却可以看作是“同人女”的自我投射。“同人女”在阅读中的自我认同分成了两个部分:一是认同于接近现实状况的卫可,一是认同于接近理想状况的谢明朗。如果说“同人女”允许自己在叙事里和欲望对象结合,那么“她”必须是以幻想中的男性自居。
《浮光》里最有意味的还不在于它的正文,而在于“番外”中对《浮光》的写作过程进行复原的元叙事部分。叙事人“我”在正文故事发生的多年后,看到了一组由谢明朗拍摄的照片。照片反映的是一对同性恋人从年富力强到年老体衰的生活过程。“番外”揭示了“耽美”制造幻觉的机制,披露了“浮光”掠过之后的真实生活,然而有趣的是,这组照片又成为“我”写作《浮光》的动因,促使“我”通过写作将残酷的现实升华为“浮光”。“番外”中的同性恋者会生病、死去,但正文里的言采却始终保持优雅的容颜,情节在二人幸福地携手后戛然而止。这种自我欺骗的幻觉正是“同人女”赖以维系“耽美”之“美”的关键,也因此,解构《浮光》正文的“番外”在同人圈子里一度备受争议。把造梦的过程展现给人看,这样的行为会引发“同人”的不悦,也在情理之中吧。
二
在一般的理解中,虚假或幻觉常常意味着需要被摧毁,从而恢复“不是幻觉之事物”【19】。但在一些持女性主义立场的研究者看来,幻觉自身充当着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因此,不应当把幻觉放在真实与虚假二元对立的层次上来简单理解,有时候,虚假是“与现存的压迫处境产生关联的唯一途径”【20】。沿着这一思路,“耽美”里看似虚假的性描写,似乎蕴含着这样的意图:以与传统言情中的异性恋迥然有别的“少年爱”来探讨一种新的人际关系。“耽美”隐晦的写作意图来自于对当下爱情现实和爱情叙事的失望。异性恋和它指向的婚姻生活日渐平庸,当恋爱的内容不断被利益填满,中产阶级的核心家庭模式变得虚伪而空洞。糟糕的现实状况扼杀了爱情在文化表达中曾被建构起来的超越性,当异性之间的爱情已然败坏之时,就必须重新想象一种不以功利理性为目的的、“纯粹的”爱情。而“耽美”恰好可以完成这个任务。它巧妙地悬置了女性的在场,隐藏起恋人们组建家庭的担忧。在这个意义上,“耽美”击中了时下爱情叙事的软肋,它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可谓恰逢其时。
由于唯美主义追求感官之乐和声色之美,这一派文学历来存在着堕入官能刺激的危险,如大正四五年的日本唯美派作家,就曾创作出一批趣味低俗的色情小说。【21】在今天,“耽美”的色情化程度比过去要高得多,但严格说来,“耽美”的根本在于“欲说还休的暧昧气息”,“尺度较大胆的小说……并不属于‘耽美’”【22】。在“耽美”的经典叙述里,单纯的欲望处于被否定的位置,只有注入了精神性的因素,欲望才有可能在“灵”的照耀下获得肯定。从中我们不难发现王尔德“灵化肉感”主张【23】的遥远回响。值得一提的是,“同性恋”和“少年爱”是两个表面上界限含混但内里截然不同的概念。“耽美bl”把“同性恋”划归为一种物质化、欲望化的关系,同时,它也竭力和异性恋的言情小说划清界限。“耽美”标举“情”的旗帜,似乎想要肃清在言情小说那里已然变质了的爱情。既然不是普通言情,不是“同性恋”,那“少年爱”意味着什么呢?
以1994年台湾电视剧《七侠五义》为原型的“bl同人”小说(以下简称“七五同人”),是大陆“耽美”界最早的“同人”作品之一。据不完全估计,网络上流传的以展昭和白玉堂为主角而创作的“bl”小说,至少有三千篇【24】。再没有比亦敌亦友的感情更能引发“同人女”“意淫(YY)”的热情了,她们乐此不疲地给这对武侠世界的侠客编写了各种爱情故事,为“耽美”界贡献了质量极高的一批小说。“toshi”是“七五同人”界以文笔老辣著称的一位作者,她有一组短篇25讲述了御猫展昭和锦毛鼠白玉堂相交的六个小故事。第一篇《分赃》,展、白二人因误会而结识,表面上相互较量,内心却极为欣赏对方。在这个故事里,展昭延续了一贯的形象,温煦和蔼,如春风拂面,白玉堂虽然鲁莽、冲动,实则和展昭一样古道热肠。在第二篇《相见》里,白玉堂在落日时分出场,暮色掩盖不住他身上刺眼的光芒。在公孙策的眼睛里看来,这怀抱金丝刀迎风而立的少年“明亮,明快,明晰,明澈,明透”,一连五个词,全部是年轻的感觉。而展昭却是个“平淡得有些淡漠的一个人”,只有当他遇到白玉堂,眉目间的飞扬才能全部回来。两个性格迥异却一样丰神俊美的年轻人,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二人如电光火石般的碰撞,绽放出“少年爱”最为眩目的光华。展、白之间,既是侠义之道的结合,也是爱与美的化身。在这两个人物形象中,“真”与“善”统一在“美”的身上,反过来说,因其之“美”,似乎也自然具备了“真”与“善”。当除暴安良的正义感最为典型地体现在展、白二人身上时,道德也变得审美化了。
“猫鼠”之恋在本质上延续的仍是“耽美”里一老一少的模式,只是二人之间的年龄差距被限定为少年人与青年人的区别。而只有和清代石玉昆的小说原著以及94年的同名电视剧放在一起比较,我们才能清楚地知道“耽美”究竟改变了什么。“七五同人”淡化了原本的主角包拯,也将展、白之外的其他侠客群体做了背景性的处理。和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中那个注重共同体的农业社会不同,“七五同人”更加突出两位主角的个体独特性。原著中展昭少年老成,白玉堂放浪不羁,但前者却谈不上羡慕后者的自由个性。展昭克己奉公,拥有值得赞美的人格,也绝非白玉堂对照之下为社会所规训的悲哀。如此看来,“同人女”对白玉堂自由个性的渲染,难道不是现代人理想自我的投射吗?而展昭的悲哀与淡漠,恐怕也粘连着她们自己面对社会时力不从心的情绪。在第四篇《曹家铺》里,药铺主人曹来祥的回忆视角使得小说充盈着淡淡的哀伤,当小说间接交代出白玉堂命丧冲宵楼之后,出现在曹家铺的展昭变得虚弱而又忧郁,连微笑起来也是:“一种春红落尽换残柯的寂寞;一种天下谁人不识君,过尽眼前无昔人的抑郁;一种举目青山出,回首暮云远,长路终难尽的无奈。”第五篇《酒客》中,展昭则因酗酒而颓唐起来,竟如文人一般得了咳症,不久撒手而去。侠客的精神依傍从公共领域的天道公理转移到私人领域的爱欲,一旦知己死去,他安身立命的东西也随之丧失,生命意义削减了大半。“耽美”里,爱情变得前所未有的重,也前所未有的轻,因为纯粹而分外美好,也因此而不堪一击。
到了“冷然风飞”所作的短篇《彼得潘》【25】,白玉堂干脆被比喻成永远长不大的男孩彼得潘,而展昭则因为执着于法理而显得不那么潇洒。二人之间有一番对话,白玉堂问展昭:“你最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展昭回答:“自然是天下太平,国泰民安。”白:“我不是指这个。我是指,你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就比如说—哪家的漂亮姑娘?”展:“这……没想过。”白:“从来没想过?”展:“没……”白:“怎么可能?一定有过!!!你啊,总是把自己埋藏起来,这下好了,连自己也找不到了吧?不过,看白爷爷我帮你把你的猫尾巴揪出来!……”直到小说结尾,展昭才承认,他“真心想要的”,不过是和白玉堂在一起的时光。
“天下太平、国泰民安”和“自己真心想要”的爱情被对立起来,个人的理想和社会的理想之间的联系断裂了,无法找到统一的媒介。“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武侠题材的“耽美”的出现,实则在根本上瓦解了武侠小说。倘若将侠客的精神寄托收缩到同性的爱情之上,那么外在的侠义之道迟早会失去存在的意义。或者不妨倒过来说,正是因为对于外在的天道和公理不再信任,“耽美”才转而将意义寄托在更为私人性的“少年爱”之上。于是,本该阳刚有力的武侠,被“耽美”改造过以后,呈现出阴柔与羸弱的面貌,慷慨悲壮的格调被一股缠绵之情浸润,踟蹰在落日时分的美少年便平添了几分颓废的姿态。
“toshi”的六个短篇展现出来的展昭之死,近乎于丧失了生之意志之后,追随恋人而去的殉情,相应的,白玉堂之死也不再被看作是对他嚣张个性的惩罚。受伤和死亡并非是使恋人们屈服的悲剧性结局,而是他们互相折磨、考验爱情纯度和浓烈程度的手段。在许多人心目里,“少年爱”唯有在相互赋予疼痛的过程中才能迸发出极致的体验,而体现这一情感的小说,在“耽美”中被称之为“虐文”。
三
“耽美”的情爱建构里,“虐”是一个核心词汇。所谓“虐”,指主人公之间的互相伤害、折磨,作者对主人公的折磨也属于“虐”的一种。虽说后来涌现出大量温馨甜蜜的作品,但从结构上讲,“甜文”多数时候只是“虐文”的治愈性补充,追求“虐”的情感是“耽美bl”兴起之初的题中之义。1960年代,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低下,受压抑的感觉被带入传统的少女漫画中,漫画作者便往往会设计出女性人物向上层社会奋斗的情节。但这时从少女漫画内部兴起的“耽美bl”漫画却反其道而行之,以美貌少年取代了女性主角,并有意在故事中制造尖锐的感情冲突。美少年之恋不再向世人许诺励志寓言,对生活的绝望情绪取代了普通少女漫画中廉价的乐观主义。【27】“bl”不接受中产阶级社会的价值观,选择用“虐”的感情形式来对抗当时日本社会虚假的主流意识形态。由此可知,以“虐”为主的“少年爱”在起源上即带有反言情、反中产阶级社会的色彩。
在早期传入中国的“耽美”中间,《绝爱》(1989年)是一部无法忽视的作品。它原本是日本漫画家尾崎南创作的动漫,后来被许多读者改编成“同人”小说,本文论及的就是一部托名尾崎南的同名长篇【28】。尾崎南的漫画原作极具惊世骇俗的个性,有人曾这样评论尾崎南的画风:彩画“多以暗色调为主,黑,灰,白,黄,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经常出现在画面焦点的一丝血红。红色的泪水,红色的指甲,红色的血,红色的伤口,触目惊心,原本就压抑的画面又多了几分血腥。”【29】这段评论准确地抓住了《绝爱》的关键意象:一片晦暗中让人绝望的腥红。小说版《绝爱》最大限度地继承了原作精神,这部作品比起其他的中国大陆原创的“耽美”小说而言,明显残留着原作里日本人激烈、决绝的气质。作品的情节很简单,它只是反复地叙写了歌星南条晃司和足球运动员泉拓人之间互相伤害又异常浓烈的爱情。作为“攻”的一方,冷漠的晃司对世界丧失了兴趣,唯独对泉怀着满腔的热情,这热情不问原因,也不会因对象的漠然态度而削弱。晃司对泉的感情带有很强的攻击性和占有性,但这也正是让许多涉世未深的少女读者入迷的地方。晃司想通过对自己和泉的不断伤害来占有对方,他甚至许诺可以通过性虐待带领泉抵达感觉的天堂。在《绝爱》的叙述表层,虐恋是和本能生命联系在一起的,带有一种反社会、反文明的意味。在人物更深层的心理当中,痛苦是人和人彼此感同身受的联系方式。晃司用一个神奇的比喻来解释这种痛感:他把自己比作身体,把泉比作可以净化全身肮脏血液的心脏,当“身体一旦感觉疼痛,心脏就会痛得跳起来”。在如此惊人的比喻里,人和人终于可以亲密无间地融合在一起了。对于居住在“甜蜜的房间”里的南条晃司而言,强烈的痛感貌似是唯一可以击碎玻璃墙的力量,它终于驱散了被毛玻璃过滤后的淡漠情感,使房间里的自我和他人发生了实际的关联。对于藻罗的那个疑问“我真的活在这个世界吗”,《绝爱》的回答也许是:如果感到痛,你就真实存在着。

文本内部的感觉冲击同时指向了文本之外。主人公因为彼此的误会、伤害以及外界的阻碍而不能结合在一起,他们获得幸福时刻的快感被延后了,而且有可能永远都无法抵达。就文本和阅读主体的关系而言,阅读虐文会给读者带来一定程度的痛苦,虐恋叙事本身仿佛也构成了一种施虐的行为。被誉为经典“虐文”的《忘欢》【30】是一个颇具哲学意味的寓言,作者以“耽美”的形式讲述了一个主和奴的故事。取名为“欢”的奴隶原本是澜国的皇子,儿时胸怀解放天下奴隶的理想,却为父兄所忌,被卖到赤国做性奴,备受折磨之后丧失了记忆。作为一个失去了表达能力和倾诉对象的奴隶,他能清楚地感受到施加在自己身上的所有痛苦,只是苦于无法用语言表达,因而也不可能产生任何仇恨或反抗的意识。通过揣摩主人的心思,他认为被主人欺凌玩弄就是快乐,就是他的名字“欢”的本义。类似这样的反讽情节是《忘欢》里写得最为精彩的地方。小说的翻转出现在接近结尾处,欢的新主人,名为“君天下”的造反者替欢实现了他幼年的理想,解放了全天下的奴隶。然而吊诡的是,君天下唯独不肯给欢自由,仍然以爱的名义奴役他。
如此诡异的历史逻辑,难怪《忘欢》会引发“耽美”小说界的“学术大讨论”。在阅读当中,给人以强烈刺痛的,莫过于欢的命运。看到高贵的前皇子饱受摧残,直到最后也没有得到拯救,是何等的心痛与惋惜!“同人女”将狠心虐待自己笔下人物的作者称为“后妈”,这个带有戏谑色彩的比喻十分贴切地揭示了她们的阅读和写作体验。据爱好“虐文”的读者说,阅读“虐文”会带来存在感。很多时候,“同人女”的“虐心”体验,是站在受虐者一方才获得的。对晚清时期林纾和王守昌一边翻译《茶花女》一边痛哭的行为,周蕾曾解释说:在受虐体验中,主体将母亲的形象向内投射进自我的幻想中,“构成了与他者有受虐性认同的时刻:当他们(林纾等)见到玛格丽特(《茶花女》主人公)承受着苦痛,他们也在苦痛之中。因为这样的回应,对于痛苦的理解成为互相交流且可逆的”。命运悲惨的玛格丽特在读者心中变成了软弱无力的婴孩,而“阅读主体变成了同情理解的母亲。”【31】于是,在同情理解的阅读行为里,“同人女”和受虐者一起体验了痛苦,获得了自我牺牲的崇高感。但是,回到《忘欢》来看,君天下实质上是处于受虐地位的人所幻想出来的人物。受虐者对改变社会现实感到无望,宁愿退回到软弱的状态,幻想由手握大权并深爱自己的施虐者来改变现状。也正是由于施虐者的“爱”,受虐者最终无法获得解放,这也成为拥有革命理想的前皇子在理想实现时所付出的必然代价。
嗜“虐”的情结并非“耽美”首创,从唯美的“前缘”来看,这种甘受侮辱的受虐体验恐怕关乎着唯美者所秉持的颓废人生观。日本唯美派先驱永井荷风出身贵族世家,年轻时却选择和家族期望完全相反的道路,投身于东京下町的江户艺道。他在一般人视为低贱的剧团里充当最底层的杂役,为人端茶倒水却乐在其中。甘受侮辱的自虐不但带给他叛逆的感觉,也让他体会到“英雄一般的悲壮”【32】。在《冷笑》里,荷风阐明了自己投身于屈辱之中的心态:“从最初就贬低自我,卑贱视之,然后才能处于超越的立场,作为一个局外者眺望周围人事。这样无论看到什么都会自然的发出冷笑。”【33】所谓从生活中退出的“超越的立场”,其实也就是一种颓废的人生观。对一切发出冷笑,意味着对一切的拒绝——拒绝自己享受高高在上的地位,也拒绝自己成为世界的同谋。颓废的人生观包含着一种否定性的精神,拒绝行为自身潜藏着某种能量。因此,颓废者首先是敏感的,倘若是感觉麻木者根本不会对自身和他人的受虐待处境感到痛苦。但和抗争逻辑截然相反,颓废者主动选择承受暴虐,而不是起而反抗暴虐。“冷笑”的旁观姿态最终又将会抵消掉那些潜在的痛苦,使人获得心理的平静。联想到《忘欢》里,联结主人和奴隶、施虐者和受虐者之间的感情中介却偏偏是“爱”,施虐者在“爱”的光环笼罩下早已不是面目狰狞,而是充满了可怖又迷人的魅力——这大概是“耽美”的态度最为暧昧的地方了。
四
历史上的唯美主义者或许向来不乏乌托邦热情,从罗尔斯到佐藤春夫,无论在现实介入还是写作虚构的层面,他们都实践了试图用唯美的理念来构建一个合理社会的想法。所以,那些认为唯美主义除了美之外不关心任何非审美事物的看法,从根本上是一种误解。【34】
与之相比,“同人女”对于“耽美”乌托邦的构想要简单得多。这个乌托邦的时间秩序是极其奇特的,似乎奉行着双重标准:时间会在外部世界流逝,却在美少年身上(至少是在外貌上)保持静止。以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为背景的《世界之灰》【35】是一部网络上称之为“世界名著风格”的“耽美”小说。作者显然对欧洲文学经典十分熟稔,整部作品像雨果、黑塞、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文学风格的杂糅。在这部作品里,当阿尔布莱希特最初见到教士莱涅时,他判定这个外表“纤细而美丽”的年轻人“有种与现实的一切都格格不入的强烈幻想和自我惩罚倾向”。多年后,阿尔布来希特再次见到莱涅,却惊讶地发现这个年轻人仿佛生存在历史时间之外,带着一种对于现实的冷嘲。几乎每一部“耽美”作品里都存活着这样一个“美人”。也许时间之于美少年最大的意义在于,历经了考验,他们仍然相爱,甚至比过去更加相爱。经验不会累积为成熟的状态,只是重复证明着最初的纯洁。“美人”的美似乎摆脱了岁月的侵蚀和物质羁绊,升华为一种关于美的理念,一种不生不灭的精神性理想。因此,对“美人”的爱,也就不能仅仅等同于世俗的爱欲,还意味着对于美的理想的永恒追求。
可是,这个乌托邦是如此的脆弱,只要作者足够诚实,他就不得不从事一项一边建构、一边拆解的工作。《世界之灰》里,革命者亚瑟和修士莱涅彼此相爱,却因信仰不同无法相守。直到他们被各自的信仰世界遗弃后再度相遇时,年轻人孤独的身心才真正地结合在一起。他们并没有安居于二人世界的甜蜜之中。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尽管外面的动荡世界布满了绞架和坟堆,但只有和那个世界中更广大的人群生发出一种血肉相连的关系,他们才能真正获得生存的意义。可惜这条通向人群的路并未走通,亚瑟和莱涅在经历了惨痛打击后,再次蜷缩回了“甜蜜的房间”。而这最后的返回,与其说是主动的选择,不如说是疲倦的无奈。在隐喻意义上,《世界之灰》像是一部“耽美”在革命后中国的发生史。在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信仰失落之后,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凸显出来,当个人无法依靠群体的生命延续来克服面对死亡的恐惧之时,唯美—颓废便成为了一条自我解救的可行之途。《世界之灰》里,亚瑟曾发誓要终结上帝建造的“没有公义的世界”,但作为上帝/父亲的叛逆的私生子,他试图“建造一个新世界”的理想也最终破灭了。小说最终归结于虚无,但这并不是《世界之灰》所达到的制高点。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莱涅面对着战争中的亡灵,渐渐觉得,在大地之下,“似乎隐藏着一个尚未被任何人察觉、然而将令人欣慰的世界,超越了所有的想象和期待。”只是他无法解释这种希望究竟源自何处。就此而言,《世界之灰》似乎看到了“耽美”乌托邦自身的局限性,它击碎了“甜蜜的房间”用以区隔个体和世界的玻璃墙,但接着它就轻易地承认无论是墙内的小世界还是墙外的大世界,都是无望的。它希冀着另一个和这两个世界都截然不同的新世界,这个新世界就存在于“耽美”的道路所无法抵达的未来。这种试图穿透黑暗、更开放地想象历史和未来的努力,也许是这个作品中最为闪亮的地方,尽管这光芒微弱而空幻。
在更多的作品那里,倘若不是悲剧的话,故事会赶在衰老和死亡降临之前,定格在“王子和另一个王子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画面。其实就算小说中人恐怕也知道,永葆青春是一个假象。没有人可以真正阻止世界的颓废,“耽美”对此能够施展的唯一魔法是暂且斩断时光之流,从中抓取出一个个稍纵即逝的瞬间加以锻造凝固,为时间赋予一种人们可以把握的空间化形式。在森茉莉一篇题为《点心闲话》的短文里,回忆中的点心便是和这样的瞬间同时出现的。她模仿自己热爱的法国作家普鲁斯特,试图在对点心的描摹中复活往昔的记忆。每当母亲要把一种名为“有平糖”的点心分给幼小的森茉莉时,“午后的阳光穿透玻璃照进来,绿叶和粉色樱花,还有赤色牡丹等等都耀眼起来,像威尼斯玻璃和水晶玻璃的碎片那样闪光。”【36】每一块精美的点心都对应一段特殊的记忆,气味、阳光、色彩混合在一起,召唤着一段青春时光。森茉莉依靠“通感”揭示出了时间的空间化形式,用这种方式向普鲁斯特致敬。在本雅明对普鲁斯特的阐释中,这种重返青春的力量和生命的衰老对称存在着:“当过去在鲜嫩欲滴的‘此刻’中映现出来时,是一种重返青春的痛苦的震惊把它又一次聚合在一起。”【37】在森茉莉笔下,浓缩了整个生命过程的瞬间的确也可以让人重返青春,但回忆主体当下的衰老境况却在笔尖语焉不详地滑走了。过去,青春被赞美,是因为它指向了更有希望的未来。现在,青春得到赞美,仅仅因为衰朽的世界将把青春带进更加无望的深渊。假如个人社会化的过程等于向现实秩序屈服,成熟意味着市侩,那么自我宁愿沉溺在指向过去的时间追忆中,而不愿意随着时间的向前而获得成长。

如果说普鲁斯特的形象在本雅明看来是“文学和生活之间无可抗拒地扩大着的鸿沟”【38】的面相,那么,森茉莉的形象就可以看作是文学以无边的想象力取代了实际生活的面相。在森茉莉的老年,她的穿着打扮却依然宛如一个女中学生的形象,见过她的人这样描述:“光看风貌,好像是骑着扫帚的巫婆;一进她心里,却永远像十六岁少女。”【39】 森茉莉以自己的生命成就了“耽美”,为此,她不惜和生活里真实的爱情擦肩而过。在她死后,人们从她的日记中得知,晚年她常去一家咖啡馆,坐在一个固定的位子上,默默注视一位咖啡馆的常客,但这个男子却从不知道邻座这位老妇人内心深藏的恋情。幻想的爱情总是比真实的爱情更美,在《奢侈贫穷》里,森茉莉写道:“现实,是悲哀的别名……人们只有活在空想中才幸福。”【40】
热爱“耽美”到腐朽程度的“同人女”会升级为“腐女”,夸张的说法是离开了“耽美”她们将无法呼吸。一个资深的“腐女”在现实中可能像森茉莉一样缺乏生活经验,与人打交道时显得笨拙。但只有极少数的“同人女”如此极端地把“耽美”贯彻至整个人生。绝大部分人在青春期过后,会回复到日常生活的轨道当中,结婚生子,把“耽美”当做青春期的事情渐渐遗忘。她们中有人认为“耽美”不过是一种休闲,有人只是跟风,还有人把它写成像言情一样轻巧的东西——现在网络上大量漂浮着的反而多是这一类作品。现在,在网上随手打开一篇“耽美”小说,人们多半发现它和普通的言情实际上没有太大区别。随着“耽美”成为一种流行时尚,它也正在日渐接近于它最初所反抗的东西。
毫无疑问,贫乏的经验是这一文学样式产生的前提,对它的沉迷反过来又加剧了经验的贫乏。但是,通过写作,“同人女”克服了现实的不完美,接近了心中美的理想。就像普鲁斯特的病床和森茉莉的公寓一样,“同人女”的电脑桌是她们笔下那个“小小的宇宙”【41】的诞生之地。正是因为现实的不完满,她们另起炉灶要再造一个更加符合内心需要的“现实”。她们的态度戏谑而非严肃,欣赏却不占有,关心美胜过其他,认同于软弱者而非英雄,当别人的幸福实现之际,也就是她们自己美梦成真之时。但是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个理想的国度从一开始排除了她们“自己”。
如今,只要听一听流行歌曲,浏览一下博客和新闻,我们就知道有多少人正在分享着和“耽美”类似的心理感受:疼痛感,遭受侮辱,软弱,绝望,认为这个世界不配拥有后代,得过且过的快乐……虽然他们不都是“同人女”,但他们对“耽美”里所书写的东西实际上并不陌生。在这个意义上,“耽美”比某些文学更加“病态”和“腐朽”,却也更接近某种心理上的真实。在异化感日益加重的时代,“耽美”的颓废姿态是一种否定,它以尖锐的不和谐音刺破了那些关于进步、现代、文明、乐观的肥皂泡泡,宣称不愿按照成年人的法则生活。但它又亲手造出了另外一些漂亮的泡泡,年轻的孩子们沉溺其中乐而忘返,把真正令人窒息的现实拒之门外。
注释:
1狭义的“同人女”指“喜欢bl(boy’s love)的女性”,和下文中许多“耽美”术语一样,这一词语直接来自于日语。2目前一些大型文学网站和“耽美”小说网实行看文收费制度(VIP会员制度),以连城读书网为例,加入VIP的小说章节定价千字3分,读者可以充值阅读。作者则依据加入V章节的订阅情况分成或以千字买断的方式获利。有些“耽美”作者每月可获得3000元的收入,有的则高达一万元。戚晓波《耽美小说初探》,《新闻爱好者》,2011年1月。3“同人志”或“同人”指由爱好者创作的、以原作人物为主要角色的作品。4陈奇佳、宋晖主编:《日本动漫影响力调查报告》,第73页,人民出版社,2009。5“攻/受”是“耽美”特有的术语,简单说是倾向于男或女。67解志熙:《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第6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812王铮:《同人的世界——对一种网络小众文化的研究》,第165页、242页,新华出版社,2008。939百度森茉莉词条,http://baike.baidu.com/view/936263.htm。10豆瓣的森茉莉小组,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8456219/。11“宅”源自1980年代日本出现的名词“御宅族”,专指沉迷于动漫、游戏和网络的人。他们极少出门,不喜欢接触陌生人,有收藏癖,大多独身。吴荇:《宅青,中国闪现闷居一族》,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http://zqb.cyol.com/content/2008-03/31/content_2124101.htm,2008年8月31日。13上田敏:《旋涡》,郭振乾、蔡彩时译,赵澧、徐京安主编:《唯美主义(外国文学流派研究资料丛书)》,第49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14威廉·冈特:《美的历险》,肖聿译,第69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5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第1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16“渥丹”:《浮光》,http://www.jjwxc.net/onebook.php?novelid=200726。17“言采”二字出自《诗经·魏风·汾沮洳》:“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无度,美无度,殊异乎公路。”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他所代表的“美无度”的“男色”。18“番外”指正文结束后的续写和补充,通常不录入正文。1920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蔡青松译,第35页,31第196页,上海三联书店,2008。21齐珮:《日本唯美派文学研究》,第72页,3233第8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22阮瑶娜:《“同人女”群体的伦理困境研究》,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16页。23在王尔德看来,爱情最美妙的境界是“天上的灵的爱和地上的肉的爱融合在一起,肉的灵化,灵的肉化,达到了交融合致的境界”。在文学作品里,王尔德充分调动艺术手段来淡化情节当中能引发情欲的因素,强调美不单纯是官能的快乐。他的唯美主义哲学是“对当时物质社会和庸人主义的一种尖锐批判”。参见徐京安《唯美主义·序》,第9—13页。24“CJ的MJ”:《MJ的鼠猫推文及阅读笔记》,http://www.jjwxc.net/onebook.php?novelid=468932&chapterid=1。25“Toshi”:《分赃》等,http://tieba.baidu.com/f?kz=336087790;《相见》,http://yanganan.blog127.fc2.com/blog-entry-5.html。26“冷然风飞”:《彼得潘》,http://www.mojian.net/bbs/viewthread.php?tid=12056。27《不暧昧的历史——BL漫画发展概论》,http://tieba.baidu.com/p/121767487。28《绝爱小说版》,四十八万字,托名尾崎南,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5903558.html?retcode=0。29“Newtype”:《解读〈绝爱〉的40个关键词》,http://www.southcn.com/cartoon/make/pl/200306260478.htm。30“玉隐”:《忘欢》,http://club.xilu.com/lovehuahua/pageview.php?boardid=0&msgno=5&url=&keywordlist=&isTopic=0。34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第187页,商务出版社,2002。35“Dome”:《世界之灰》,百度浅浅寂寞吧,http://tieba.baidu.com/f?kz=171573091。36森茉莉:《点心闲话》,豆瓣森茉莉小组,http://www.douban.com/note/77487632/。3738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第226页,41第230页,三联书店,2008。40“ATOM”:《奢侈品穷之茉莉流魔法》,http://atomcorner.blogs.com/blog/2004/09/_.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