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保马”
今天(2016年10月16日)是路易·阿尔都塞诞辰98周年纪念,保马特别推送阿尔都塞的文章《作为“有限”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在这篇回复罗桑达的文章中,阿尔都塞指出,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并非一个抽象的结果,而是具体地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缝隙中。这种趋势只有借助阶级斗争才能够获得其现实性。马克思主义不同于历史哲学之处,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一门“有限”的学说,它并不对未来做出任何弥赛亚式的保证:正是因为这一点,马克思主义才能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种种矛盾趋势开放,并向着不可预见的意外开放。在关于“政治”的问题上,阿尔都塞认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机器构造出了政治社会(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区分,继而在其构造出的政治领域内污染了种种反抗运动的形式。因此,必须要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概念及其实践所塑造的政治。在这个意义上,党只有区别于政党,进而独立于(大写)国家,才能最终走出资产阶级(大写)国家。这在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应该是“有限”的:它关系到阶级斗争能否摆脱关于总体性的潜在唯心主义学说或“政治的法律幻觉”的干扰。
文章原载于《马基雅维利的孤独》(伊夫·桑托梅编,法国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1-296页。全书中译本将由西北大学出版社收入“精神译丛”第二辑出版。感谢译者赵文老师授权保马首发。
赵文 译
法文编者按
本文最初以意大利文发表在1978年4月4日的《宣言报》上。写这篇文章为的是答复罗桑纳·罗桑达在1978年3月12日也就是在阿尔都塞出席“威尼斯论坛”引起争议后不久提交给他的一份书面要求。罗桑纳·罗桑达当时是《宣言报》的主编。[1] 阿尔都塞在发言中曾明确地说在马克思那里不存在任何国家理论,而这个提法在意大利左派那里引发了公愤。因此,《宣言报》建议《保卫马克思》的作者“再回过头谈谈您的这个论断,在威尼斯它还只是个悬而未决的提法,特别是考虑到此前在意大利左派当中就一直存在的争论,尤其还有在《世界工人》(Mondoperaio)上发生的争论——这场争论在朱利亚诺·阿马托和皮特洛·英格劳的对谈发表以及《再生》杂志最后刊载比亚吉奥·德乔万尼那篇文章之前一直继续着。”[2]
《世界工人》是意大利社会党的理论月刊,在更早些的时候在这个刊物上就发表了N.博比奥(N. Bobbio)的两篇文章,在整个意大利引起了巨大反响[3]。哲学家卷入这场争论时,这场争论已经在欧洲范围内大规模展开了,就是在这时他通过某种修正了的努力明确指出,只要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开始思考民主国家,那么它就是可疑的。尽管他的观点建立在严肃的而非论战式的论证基础之上,但其理论的进攻性却在意大利左派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当中激起了一系列反应。与意大利共产党有关的那些人在意共的理论周刊《再生》上发起了反击。那时博比奥也对自己的诋毁者进行了回击。[4] 全部争论尽管明显带有它形成于其中的特殊经济形势的烙印但却是成果丰富的。非常可贵的是我们看到,这次争论只把自己限制在政治哲学层面和对政治策略及政治认同的讨论之上,从而避免了介入各方极力想把这两个层面以一种协调一致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愿望,也没有出现某方以统一的方式主导这次反思的现象。这次讨论在法国只产生了一点微弱的回响。[5] 回过头来看,我们可以这么说,在这次大讨论当中博比奥获得了最终的胜利。相关的全部文献当时就由《世界工人》汇集出版。[6]
阿尔都塞的文章承继了此前就开始的那场论争,同时在《宣言报》上又引起了争论,但可以看出,这次讨论的方向已经有所改变。阿尔都塞所引发的这场争论继承了博比奥通过提出左派的自由难题发起的理论进攻,这进攻完全是针对意大利共产党那里的“马克思主义正统”的,不过现在,阿尔都塞通过这场争论提出了几乎称得上是“绝对自由主义”的难题。
罗桑纳·罗桑达向他提出了如下问题:
出席威尼斯会议时您指出,马克思那里不存在国家理论。我也同意这一点,尽管在马克思那里存在着一种反向理论——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是什么——并且以零散的方式存在着一些有关现代国家的分析,这些分析较之列宁那里的分析要充分一些。不管怎么说,争论不是哲学性的,它是这样一个阶段里的当务之急,此刻,各种“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危机已经显而易见,意大利共产党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共产党要么合并进入了政府,要么正在打算这么做。
基于在意大利展开的争论,我们可以提出许多问题。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其中一个问题。在1976年12月的索邦大学讲演当中[……],您曾特别强调不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就不可能抛弃[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在你看来,“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当中哪些方面发生了危机呢?可能存在两种探讨的方向。一种坚持认为,这些社会成员还相对不成熟,因此必须有一个国家以构成一个统一的政治领域[……]。但是它意味着在社会主义当中,“不成熟”使得旧式国家成为必需,甚至这种国家比现代国家还要更为集中化,是这样吗?相反,另一种探讨方向则关注的是共产主义过渡阶段中“政治领域”的理论形式。这种政治领域的形式必须经过使自己成为国家本身并作为补充包含了各种内部倾向(正如你在索邦用是或不的说法所说的:倾向,是的;宗派,不!)的党,我们必须承认——就像谈到意大利时必须承认的那样——这一点吗?它是否有利于各个不同的社会基础在政治上表达自身[……]?在这种条件下,政治和工人阶级政党之间将有着怎样的关系?
明确地说,何为过渡阶段的政治?[……]换言之,时时处处有矛盾对立的社会(毛),如果没有规章制度,总是永远停留在不平衡阶段,处在无法区分出左中右因而也是将社会辩证法搞得一团混乱的斗争之中,它还能存在下去吗?“法权”、“国家”,它们作为某种妥协形式出现在每个社会阶段,包括过渡阶段,难道不是吗?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将以何种方式在什么时候消亡?究竟是什么让我们认为“生产者”将不再需要某种“普遍的”政治中介?[7]
阿尔都塞的这篇文章招致了法国共产党的极大愤慨,猛烈地批评这篇文章说它 “伤害”了“法国共产党人的感情”,法共还对《宣言报》提出了强烈的质疑。[8] 文章也在《宣言报》的专栏上引发了大量的讨论,欧洲和意大利的许多左派知识分子都参与其中。报纸上全部讨论章在稍作修改之后汇集出版,标题为《关于国家的讨论(由路易·阿尔都塞的论点引发的立场之争)》[9]。法国刊物《辩证法》还以“访谈”的标题发表了本文的一个删节版。[10] 《辩证法》与J.T.德桑蒂(J. T. Desanti)和阿尔都塞两人都有着很深的渊源,这个刊物作为一份独立的理论杂志在20世纪70年代迅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1]。直到最后一刻阿尔都塞又改变了主意,不愿以法文发表这篇文章,甚至想把这期杂志全部买下,但遭到了凯塞格吕贝的拒绝,最终只好听之任之了。
严格地讲,“作为‘有限’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篇访谈,而是由R.罗桑达提出的问题引发的书面文本。我们下面刊出的版本的基础就是《宣言报》上意大利译文所本的打印稿。《辩证法》上所发表的那个删节版当中不是在文风上有所改动,就是在侧重问题上做了较大调整。此外,这个删节版的完成稍早于《宣言报》所使用的打印稿,在后者当中出现的一些手写修订却不见于这个删节版。我们将在编者注当中说明我们所选用的版本与《辩证法》上发表的版本之间的主要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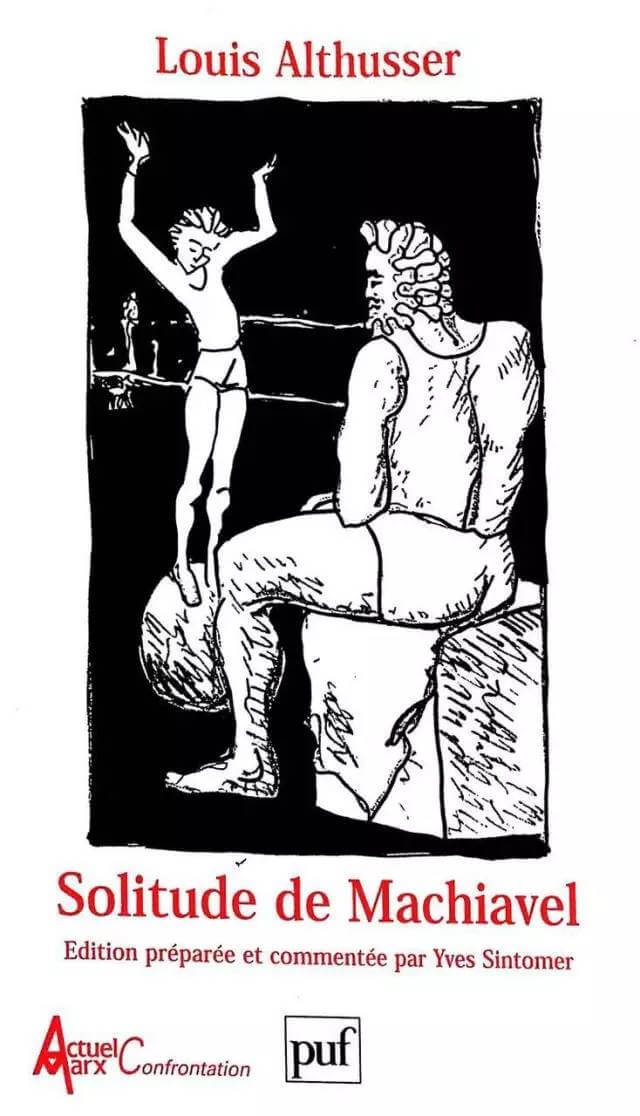
您向我提出的那些问题以某种形式,特别是以某种术语系统被表述出来,这种形式和术语系统实际上包含了一系列有关国家和“市民社会”、政治、(大写)国家消亡等马克思理论的假说。要细致地考察您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就必须首先对这些假说进行解释。因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它们根本不是来自他本人的a。
1.绝非偶然的是,在阅读英格劳和德乔万尼的文章时,我总是碰上形容词“complessivo”b,这个词一再地出现在我们这两位同志(也还有其他同志)的政治文本当中,我总是碰上这个“整体性”概念,但在我看来,这个词与另一个同样常常出现的词“一般性”(“一般契机”,等等)不是没有关系的。我在这些词背后,同样也在潜藏于这些词之后的那种看法当中,辨认出了这样一种观念,即马克思主义学说能够“涵盖”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全部过程,进而实际上意味着在现有过程中有某些矛盾的趋势在起作用。自从摆脱了他青年期作品的预言倾向和乌托邦社会主主义倾向之后(应该说这种倾向在《资本论》的某些观点中还一直存在着),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趋势。这一趋势不是一个抽象结果。实际的共产主义形式都来都具体地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缝隙”之中(这有点像交换的商业形式存在于封建社会或奴隶社会的“缝隙之中”):具体地存在于相对而言规避商业关系的那些联合体当中c。
在这个问题背后,存在着一个相当重要的理论难题。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有限的”和有边界的。它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和其矛盾趋势方面是有限的,而正是那种趋势打开了废除资本主义、用“其他的东西”取而代之——这种取代已经在资本主义社会缝隙当中成形了——的过渡可能性。说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有限的”,也就是支持这样一种基本的观念,即马克思主义学说与历史哲学不同,这种历史哲学,在实际思考过程中,“涵盖”了全部的人类未来,并且因而能够事先以实证的方式确定这个词: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说(如果我们摆脱了历史哲学的诱惑的话,马克思有时候也向这种诱惑投降,这种诱惑在第二国际那里在斯大林时期,占据着压倒性的支配地位)应该属于并限定在现阶段:资本主义剥削的阶段。对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系列现象当中可以观察到的一种当前趋势、(大写)共产主义趋势可能性(生产向“间隙”形式的社会化发展可能性)做虚线式的、消极的延长,就是我们有关未来所能说的一切。应该看到,我们必须从被理解为过渡(无产阶级专政——条件是不要对这个词做出具有倾向性的错误解释d)和(大写)国家的最后残余的现有社会出发。就所有被称为过渡的情况而言,它所包含的只能是某种实际趋势所能表现出的各种情况,这种趋势,就如在马克思那里的所有趋势一样,如果没有阶级斗争政治赋予其现实性就只能“被挫败”而无法实现。这种现实性不可能现在以确定的实证形式得到预言:只有在斗争过程之中,各种可能的形式才能来到世上、提上日程、被发现并成为现实。
在这些情况下,承认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有限的”,也就完全排除了一种封闭的学说。只有历史哲学才是封闭的,因为它实现在其思想之中堵塞了所有历史的过程。只有“有限的”学说才真正向着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察觉到的各种矛盾趋势开放,并向着它们的不确定的命运开放,向着不断给工人运动打上标记的那些不可预见的“意外”开放,正是因为开放才细致入微,并能对不可救药的历史想象进行严肃的思考,进而用时代与它对质e。我因而相信,必须彻底抛开仍可在列宁,以及葛兰西那里看到的某些表述中存在的这样一种思想,即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总体”理论,具有在(大写)绝对知识的实践当中达到顶点的历史哲学的形式,并且能够对尚未提上“日程”的难题进行思考,具有独断地预见这些难题之解决条件的形式。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一种“有限的”学说,其出发点是对其自身边界的明确意识,唯其如此,它才可能提出绝大多数属于我们的主要难题。
另外要补充一个事实,它本身对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关系重大,即马克思主义学说很少谈及(大写)国家,也很少谈及阶级斗争的(大写)意识形态及各种意识形态,没有涉及阶级斗争的政治,也没有涉及阶级斗争的组织(它们的结构、它们的功能)f。这个“盲点”反映了马克思走不出的理论边界,他仿佛被(大写)国家、政治……等等这样的资产阶级表述麻痹了似的,甚至只能以否定的形式再生产这样的表述(对其法律性质的批判g)。盲点或禁区,结果相同。这非常重要,因为共产主义趋势在所有这些“区域”或难题当中都是被堵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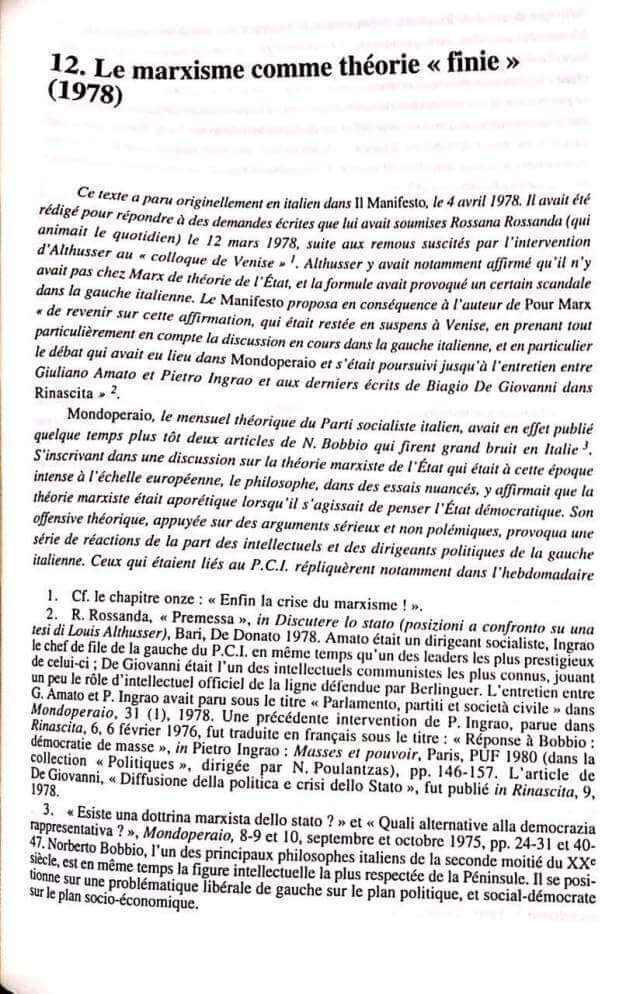
2.第二个假说涉及“政治”。在我看来,葛兰西重提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这一旧的资产阶级区分——尽管自有其深刻的历史意义h,甚至尽管他为市民社会这个概念赋予了另一种意义(建立在“公共”和“私人”这一现有法律区分基础之上的“私人的”领导权,进而也是独立于与“政治社会”等同的“国家领域”之外的领导权i),但也因此遮蔽而非澄清了马克思的这个盲点。在我看来,就意大利讨论的难题性来说,政治社会、国家、与“私人”(和“个人”,尤其是与德乔万尼提到的“局部”完全不是一回事,虽然他也使用“私人”这个词j)相对的“普遍化”作用等概念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我认为,相互关联的这些概念的集合要么返回到资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概念(及其实践)当中,要么就返回到有关作为实现了的“总体”的“国家的普遍性”,或最终从“剥削”、劳动分工和压迫(领导者/被领导者)当中解放了的人的总体性的潜在的唯心主义当中,马克思在接受费尔巴哈遗产的青年创作期的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其后一段时间里都在追随着这种唯心主义:人的本质的基础存在于(大写)国家当中,而(大写)国家则以异化了的普遍性形式表现着人的本质,只要意识到并进而实现一种好的、非异化的“普遍性”形式就够了:路的尽头不过就是改良主义k。
然而,这里有一个在我看来非常关键的要点:在(大写)国家当中争夺赌注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此时此刻的)阶级斗争是事实,但绝不意味着政治就一定要根据其与(大写)国家的关系得到确定。必须仔细地将无产阶级的政治和它的直接赌注区分开来l。正如马克思将《资本论》审慎地表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样,我们必须达到这样一个从未达到过的目标m:对资产阶级政治的意识形态概念和实践所强加的那种“政治”进行“批判”。正是从资产阶级观点来看,才能看到在“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区别:这种区别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来说是构成性的,并被资产阶级当作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借由政治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强行确立(源自个人意志的普遍意志,通过投票昭示给所有人,并被最高法院所“代表”)n。同样我们可以说,从资产阶级观点来看,(大写)国家被表述为一个与其余领域分离的“领域”,完全不同于(无论是在黑格尔意义上的还是葛兰西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独立于市民社会。请想一想这种意识形态观念,这种自有其特殊利益所系的意识形态观念,与简单明了的现实——即使是法律观点下的现实o——是根本不相符的。(大写)国家总已经深深地(从两个方向)渗入市民社会当中,不仅通过货币和法权,不仅通过压迫性机器的在场和干预,而且通过其意识形态机器。在经过长期思考之后,我实际上能够——尽管有葛兰西的细致分析——保留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个概念,因为在我看来它比葛兰西的领导权机器更精确,后者只是通过其效果(领导权)来界定该机器,而未提到该机器功能——意识形态——是什么p,保留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个概念才能够细致地察觉,领导权的行使形式——即便这些形式的“起源”是自发的和“私人的”——被整合到并改造成了意识形态的形式,后一种形式与(大写)国家有着有机的关系:(大写)国家可以随时随地“找到”这些形式,或多或少是无形式的形式,它们总是已经发生于历史之中的形式,(大写)国家无须去生产它们而只须“与它们相遇”:(大写)国家不断地整合—统一它们以使其适合为领导权提供保证。在这种整合—改造也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得到确立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发挥着支配作用的乃是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之实践有着密切关系的某个特定意识形态领域:为了实现资产阶级领导权,法律意识形态发挥着这个聚合和综合的作用,这个聚合和综合过程绝不能理解为完美的,而只能理解为充满矛盾的,没有被统治的意识形态,就没有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也带有这种统治关系的烙印q。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似乎就是,由于(大写)国家(也就是说法律)乃是阶级斗争的最后赌注,所以人们将政治化简为其赌注构成的这个“领域”。与这种幻觉,这种直接源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将政治化简为其赌注的那种观念的幻觉不同,葛兰西很好地理解了“一切都是政治”,因而不存在“政治公共领域”,政治社会(或[大写]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区别很好地说明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及实践所强加的那些形式,而工人运动必须终止这种幻觉及其形形色色的伪装,对(大写)国家的概念和政治形成另一种看法。
就(大写)国家而言,首要的问题是,不能将其现实性化简为仅由其机器构成的可见领域,即便这些机器潜藏在(大写)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剧场(政治“体系”)的背后。(大写)国家过去一直在“扩大”,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看清那些指出这种“扩大”是一个新现象的人的含混之处,这种含混将彻底改变问题的全部实际情况。实际上,这种扩大的形式一直在改变(当然,是那么频繁!),但扩大的基本原则却没变过。在我看来,直到最近,他们对国家的扩大一直视而不见,尽管这种扩大在绝对主义君主制(不用往更古老的时代追溯)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当中都是显而易见的。
就政治而言,首要的问题是,不能将政治简化成资产阶级官方承认为政治的那些形式:(大写)国家、人民代表制、政党、为占有现有国家权力而进行的政治斗争等等。如果我们进度到这种逻辑,如果我们还停留在这种逻辑之中,那么我们不仅有可能陷入到“议会幼稚病”(已经讨论过了),而且尤其可能陷入到政治的法律幻觉之中:因为这种政治体现着法律,而这种法律又规定了(并且仅仅规定了)体现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包括党派活动在内的——那些政治形式。有一个本地的例子,虽然它还比不上在意大利发生的事情:在法国,雇主们针对来到工厂车间与工人们交谈的共产主义者提起了一系列的诉讼:雇主有权提起这些诉讼。当然,这种政治和“社会”权利因那种细致地将政治和非政治区别开来的法律意识形态而得到了加强。这种意识形态并非是一些“观念”,相反它是——比如说——通过国家意识形态的工会机器而实现的:有那么多工会吸纳了追随着非政治的工会意识形态的工人(其方式就是对工人反对资产阶级政治的必然要求加以盘剥利用:比如说无政府工团主义)r。
这里问题的关键不是“扩大”现有政治,而是要知道务必留意政治究竟源自何处,究竟是在哪里被生产出来的。将政治区别于其资产阶级法律身份的趋势目前已经成形。党派/工会的旧有区分正经受严峻的考验,独立于政党,甚至独立于工人运动,发生了许多彻底令人意外的首创运动(生态学、女性斗争、青年斗争,等等),这些运动诚然相当混乱,但却不乏成就。英格劳所谈到的“普遍政治化”是一个症状,必须被解释为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形式的质疑,这种质疑虽然粗陋,但意义重大。所有这一切的实现,通过了激烈的矛盾,但这些矛盾实际上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即便它们的鼓吹者并不这么认为s。从这种观点来看,意大利处在首创的前沿地带,我很乐意通过这一点而将意大利共产党难于整合某些新运动甚或难于与它们取得联系的种种困难解释为政治和政党的传统观念受到质疑的一种信号,并将工会的种种政治首创运动——这些运动有时只是临时将党卷入其中——解释为一种警报:党必须告别那种旧有观念t。当然,所有这些运动最终都会对党的组织形式本身提出批评,我们发现(有点晚了!)它恰恰是按照资产阶级政治机器的模型建立起来的(这样的组织有它讨论事务的最高法院:在 “基层”和它的被选举出来——无论选举是否举行过——的领导之间则是层层中介,从而通过官僚机构机器并以巩固高度一致性的党的团结的意识形态确保党的“路线”的统治地位)u。显而易见,资产阶级的政治观念所造成的这种深层污染是影响着工人组织未来的关键。

3.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我很容易在面对如下这类提法时感到不安:我们总是假设过渡期的“政治领域”的理论形式“必须经过构成(大写)国家的党”。确切地讲,在我看来根本不可能承认这种思想(如果我没搞错的话,葛兰西曾在《现代君主论》的理论中曾为这种思想进行过辩护,他实际上恢复了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当中的一个重要主题——马基雅维利曾很好地表述过这个主题)。要说党“构成(大写)国家”,我们有苏联。我在很久以前曾对意大利朋友说过,从原则上来讲,千万千万不能把党看作是“一个政府党”——即使在某些情况下它可以参与到政府当中。从原则上讲,根据党的政治的和历史的存在理由来看,它必须独立于(大写)国家而存在,不仅是资产阶级(大写)国家,更重要的是无产阶级(大写)国家v。党在政治上相对于国家的外在性是一项基本原则,我们可以在马克思和列宁不多的几篇文本中发现这个问题。(将党与[大写]国家相分离使之回归人民群众,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所做的绝望的尝试。w)如果没有党(而非政党)相对于国家的这种独立性,我们将永远无法走出资产阶级(大写)国家,不管它再怎么如我们所愿地被“改良”。
正是党相对于(大写)国家的独立性能说明形式上被称为“多元主义”的东西的可能性(或必要性)。在过渡期内众多政党完全有有利条件存在下去:这将是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领导权形式之一,但有一个条件:工人阶级的政党与其他政党不同,也就是说不是政治的国家意识形态机器(议会体制)当中的一部分,而从根本上讲通过它在人民群众中的活动独立于(大写)国家,它要将催生资产阶级(大写)国家机器的瓦解—改造以及新的革命(国家)的消亡的运动引入到人民群众当中去。
头号陷阱就是(大写)国家:无论这国家采用的是阶级合作或现有“法制”管理的政治形式,还是采用的是党的“未来国家”的神话形式。我是从理论观点才称其为神话的,因为非常不幸,在众多“社会主义”国家当中这种形式太现实了。
我知道要“坚持”这种政治立场殊为不易:但不如此,党的独立性就会无可挽回地受到损害,既摆脱阶级合作又摆脱国家—党及其后果的风险的可能性也将不复存在。
但如果我们设法保持了这样的立场,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向我提出的那类问题在我看来就能得到恰如其分地对待:当然,过渡时期的(大写)国家完全有必要建立、尊重和执行保护人民和国家的反对者的法律“游戏规则”x。而即便党是独立的和被排除在外的,它也要尊重它的对话者们所理解的——根据资产阶级古典意识形态所理解的——“游戏规则”,尊重“政治领域”——其方式必须是在决定一切的那个方面,即群众运动方面,来从事政治(fare politica)。摧毁资产阶级国家并不是废除一切“游戏规则”,而是要彻底改造其机器,废除一些,创造另一些,使之全部革命化y。我们不能指望在对“游戏规则”的限制或废除(正如苏联做的那样)当中能体现人民群众的行动,除了终有一天会转变为悲剧的粗陋的那些形式z。游戏规则,古典思想家们构想出来的这类游戏规则,乃是另一场游戏的一部分,那场游戏远比这场权利游戏更为重要,博比奥本人是清楚地知道这一点的。如果党保持它的独立性,那么它尊重并提倡游戏规则的时候所能获得的将是一切同时又将一无所失。当游戏规则必须改变的时候,它将能够以最大的自由度、在(大写)国家消亡的方向上做出响应aa。但如果党失去了它在阶级、首创性和行动方面的独立性的话,这同一些“游戏规则”就不再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是为完全不同的利益服务了bb。
既然这是一个“游戏规则”的问题,前面也曾谈到过它也是作为趋势和“缝隙间”存在的现实的共产主义的问题,那就有必要来谈一谈这个“遥远的未来”,它有可能永远不会发生,尽管已经在我们社会的空隙之中成形。人们往往执着于诸如马克思所谈的继“必然王国”之后出现的“自由王国”(!)、“人的自由发展”和“自由联合体”之类的唯心主义表述。我姑且这样说吧:共产主义意味着出现这样一种个体,他最终从道德意识形态重担当中解放出来,这使他成为了一个“人”。但我不确定马克思是否也这样理解。个体的自由发展,以及最终消除了拜物教不透明性的社会关系的“透明性”,都是马克思用来说明这个无限接近过程的证明。并非偶然的是,共产主义看上去似乎就是拜物教的对立面,是其中体现着拜物教的一切现实的对立面:在作为拜物教之颠倒的共产主义图景当中,看上去就存在着个体的自由活动、他的“异化”的终结、他的一切异化形式的终结、商业关系的终结、(大写)国家的终结、(大写)意识形态的终结、政治本身的终结。极言之,这是一个没有社会关系的个体社会。
即便这是一种展望——也必须在这样的条件下来理解它,我们也应持最基本的谨慎态度,不应接受有关人的存在、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自由的条件之透明性的这幅亚当式图景。即使共产主义将会存在,它也有着自己的生产关系——这种关系必然会被称为“生产者的自由联合体”,因而有着它自己的社会关系,并且也有着他自己的意识形态关系。即使这种社会最终摆脱了(大写)国家,而不能说它将见证政治的终结——当然,会见证资产阶级最终形式上的那种政治的终结,——但这种政治(它是马克思唯一瞄准的政治,直至消失在他的“盲点”之中)将被另一种政治取代,那将是一种没有(大写)国家的政治,只要承认甚至在我们的社会中政治与(大写)国家也是不可混淆的,则不难想象这种政治了。
在我看来我们没有理由投入到这场小小的理论游戏当中。然而经验表明,即便是有关共产主义最通俗的的表述——它就弥散在人们,特别是共产主义者的心灵当中——是与他们的构思方式和现存社会、与他们的直接的和最切近的斗争相一致的。对共产主义的想象并非是清白的:它将滋生为目前行动的形式和未来走向提供担保的那些弥赛亚幻想,这些幻想将让他们偏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它还可能保留空洞的“普遍性”概念,在“一般契机”之类人为的含糊之词当中就能找到这种空洞概念,通过它,普遍利益的“一致性”将得到满足,就像“社会契约”的普遍性所勾勒的古老的蓝图终有一天将会在“管控社会”中成为现实似的。这种想象最终让这那些可疑概念得以存活(或幸存),正是通过那些概念,按照毫无理论可言的直接宗教模型,马克思思考着拜物教和异化。——这些概念先满篇充斥于《1844年手稿》,随后有固执地重现于《大纲》,并在《资本论》中仍然保留了它们的痕迹。要解开这些概念的谜底,必须参考马克思就共产主义形成的想象:我们可以通过使这种难题性想象服从于唯物主义批判的方式尝试着开始解析它们。通过这种批判,我们将开始能够对马克思那里还受着有关历史(大写)意义的唯心主义影响的东西进行定位。这是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值得下一番苦功的挑战。
4.对我来说,要进入意大利正在进行的有趣讨论(阿马托—英格劳—德乔万尼)是非常困难的,即使只是出于政治语境的原因……因为我们的同志们是通过从葛兰西的概念坐标出发形成的细致而抽象的术语体系来思考的,这种属于体系让我们、我们这些法语方言者面临着巨大的交流难题cc。
我应该说,当英格劳强调有必要尽最大可能对在党外发展起来的原创运动予以关注的时候,当他注意到党的态度变化(拒绝一切总体化的观点)的时候,当他说应以新术语提出政党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的我和他是非常接近的。但是,当他在谈到某种程度上在任何政治范围内都是构成性要素的(大写)国家和政治领域dd的时候,当他谈到政治的“社会化”——还不如说(他在别处也说过)“社会的政治化”——的时候,我是持相当保留意见的。因为谈论“政治的社会化”的前提是一种政治,一种可以被社会化的政治的先行存在,而这种 “社会化”的政治因无论如何也应该是具有占支配地位形式的那种政治。在我看来非常有意思的是,在英格劳所援引的例证当中,实际上,事情完全颠倒了过来:不是政治适应人民群众,而是群众适应政治,并且首要的是适应“新的政治实践”(巴利巴尔)。正是因此,当我看到英格劳宣称那些运动的冲突性和多样性“赋予一般性中介的契机以更大的重要性”的时候,我才感到非常失望。我遗憾的是,他用如此抽象的术语说话,以至于给人的印象是他在强调一般性的(大写)国家,而未能摆明对它的改造。这也许是来自葛兰西的一个偏向,他倾向于将(大写)国家机器混同于其功能,而未充分注意国家的物质性层面ee。
我在乔万尼那里找到了类似的说法(socializarre la politica ; diffusività della politica nel « particolare » ; diffusione molecolare della politica,等等),我虽然对这些说法以及他的“diffusione dello Stato” ff学说——该学说很容易让人想到“(大写)国家扩大”,也容易将(大写)国家与政治(参考前面)混为一谈——持保留意见,但当看到他提到“那种政治的独立性的危机”,特别是看到他把那种政治定义为“旧有(大写)国家的理论和实践形式”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与他是相近的。因为此时他用其本身的名字来称呼政治:就位了的领导权形式。当他非常正确地指出“对这种政治中介的颂扬孕育了内含于其‘扩散’当中的脆弱的风险”的时候,我与他是意见一致的。这是一个关键之点:政治不会不“扩散”(不言而喻:自上而下地、从[大写]国家和政党形式开始扩散)到这样一种危险的程度,受到技术主义的威胁或沦为让它在(大写)国家权力的“墙”上碰壁的一种“参与”(既然[大写]国家自己也能组织这种参与!)。“只是通过独立性自治来应对历史地存在的权力的‘普遍性’[在这里德乔万尼是用它自己的名称来称呼这种‘普遍性’的]似乎是不充分的。关键之点从来都是领导权,它之所以被接受,乃在于具有那种可以在其中指明建国方式的总体形式。”
我很难接受“总体形式”——但不包括领导权——和建国的说法(即便是在推翻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同时建设革命的国家):在这里gg,这些词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因为必须对德乔万尼“用密码写成”的这篇文章进行破译——向我们言说着长久以来就为人所知的事情hh。
原编者注
法文编按部分
[1] 参看第11篇“马克思主义终于危机了!”。
[2] 见R. 罗桑达:“导言”,载《关于国家的讨论(由路易·阿尔都塞的论点引发的立场之争)》(Discutere lo stato (posizioni has confronto known una tesi di Louis Althusser, Bari, De Donato 1978)。朱利亚诺·阿马托(Giuliano Amato)是社会党的领袖,而皮特洛·英格劳(Pietro Ingrao)则既是意大利共产党享有盛誉的领导人之一又是党内左派的领导,比亚吉奥·德乔万尼(Biagio De Giovanni)是最知名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对贝林格(Berlinguer)的知识分子官方路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阿马托和英格劳的对谈以“议会、政党和市民社会”(Parlamento, partiti et società civile)为题发表于《世界工人》1978年31(1)卷。英格劳更早些时候的讨论介入发表在的《再生》1976年2月6期上,此文法文译本的标题是“答博比奥,论大众民主”( Réponse à Bobbio : démocratie de masse),收在皮特洛·英格劳:《群众与权力》(Masses et pouvoir, Paris, PUF 1980)第146-157页(此书是普兰查斯主持的“政治学丛书”(«Politiques»)当中的一册)。德乔万尼的“政治宣传和国家危机”( Diffusione della politica e crisi dello Stato)一文发表在《再生》1978年第9期上。
[3] “存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吗?”(Esiste una dottrina marxista dello stato ?)和“代议制民主的替代方案是什么?”(Quali alternative alla democrazia rappresentativa ?),载《世界工人》1975年9月和10月8-9卷和10卷,第24-31页和第40-47页。诺贝尔托·博比奥(Norberto Bobbio),是20世纪后半叶意大利最主要的哲学家之一,他同时也是意大利半岛知识界最受尊重的人物。他向左派提出了政治规划的自由问题以及社会-经济层面的社会民主的自由问题等一系列难题。
[4] “什么是社会主义?”(Quale socialismo ?),载《世界工人》,1976年5月5期,第55-62页。
[5] 在法国,刊物《辩证法》(Dialectiques)起到了关键作用,特别是它在18-19卷以“意大利和我们”为题发表了曾刊于《世界工人》和《再生》上的主要争论文献。除了尼科斯·普朗查斯撰文参与之外,É. 巴利巴尔、C. 卢波利尼(C. Luporini)和A. 多塞尔(A. Tosel)也在“理论丛书”里发表著作《马克思及其对政治的批判》(Marx et sa critique de la politique, Paris, Maspero, coll. « Théorie» 1979)参与讨论。尽管普朗查斯深受阿尔都塞的影响,可在当时还是形成了与阿尔都塞在“作为‘有限’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当中引入的思考方向完全相反的思想,他竭力主张将国家视为社会权力斗争的“凝缩”关系的研究策略。参看:N.普朗查斯自选集《国家的危机》(La crise de l’État, Paris, PUF 1976);《国家,权力,社会主义》(L’État, le pouvoir, le socialisme, Paris, PUF 1978);“辩证法-介入”丛书中的《参照:昨天和今天》(Repères: Hier et aujourd'hui, Paris Maspero , coll. «Dialectiques-Interventions» 1980)。
[6] 《〈世界工人〉手册》,新丛书,第四辑(Quaderni di Mondoperaio, nouvelle série, 4):《马克思主义和国家:意大利左派对诺贝尔托·博比奥论点的公开讨论》(Il marxismo e lo stato. Il dibattito aperto nella sinistra italiana sulle tesi di Norberto Bobbio),这部文集中除了博比奥的那些文章之外,还收录了塞隆尼(Cerroni)、波法(Boffa)、杰拉塔纳(Gerratana)、奥克托(Occhetto)、英格劳、奎杜奇(Guiducci)、塞滕布里尼(Settembrini)、迪亚斯(Diaz)、维卡、西尼奥里莱(Signorile),鲁福洛(Ruffolo)和马基奥罗(Macchioro)等人的相关文章。博比奥还把自己的争论文章专门结集出版:《什么是社会主义?》(Quale socialismo? Turin, Einaudi 1976)。
[7] 《宣言报》,1978年4月4日。他在文中提及阿尔都塞1976年12月16日在索邦大学与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UEC)公开讨论前的演讲后来以“22大”为题在“理论丛书”当中出版(22e Congreès, Paris, Maspero, coll., « Théorie » 1977)。
[8] 见《人道报》,1978年4月8日。
[9] 文集《关于国家的讨论(由路易·阿尔都塞的论点引发的立场之争)》当中除了阿尔都塞的文章“作为‘有限’学说的马克思主义”(Il marxismo come teoria ‘finita’,第7-21页)之外,还收入了以下作者的争论文章:维卡、梅纳帕切(Menapace)、康帕尼亚诺(Campagnano)、德乔万尼、卡瓦祖蒂(Cavazzuti)、蒙塔纳里(Montanari)、巴达洛尼(Badaloni)、康比(Campi)、博比奥、左洛(Zolo)、费斯特蒂(Fistetti)、莱昂内(Leone)、德卡斯蒂里斯(De Castris)、罗瓦蒂(Rovatti)、帕斯夸雷利(Pasquarelli)、鲁普利尼(Luprini)、费彻尔、德·布伦霍夫(De Brunhoff)、阿尔特瓦特(Altvater)、卡尔朔伊尔(Kallscheuer)、泰洛(Telo)、埃德尔曼(Edelman)、马拉马奥(Marramao)、巴利巴尔、比基-格吕克斯曼(Buci-Cluksmann)和罗桑达。与阿尔都塞争论的文献综述以法语发表在《辩证法》1978年第四季度24-25卷的档案记录当中。
[10] 《辩证法》,1978年春季,第23期,第5-12页(这个版本所署的日期为1977年11月,这是错误的)。
[11] 其发行量超过了10000份(参看F.多斯:《结构主义史》,第二卷,第209-210页)。辩证法的主编是D.凯塞格吕贝(D. Kaisergruber)。
正文部分
a 最后这两句话被删掉。
b 我们可以用“普遍”、“总体”、“全体”来翻译complessivo一词。
c 最后这两句话被删掉。
d 这一段与被删掉。
e 此段删除。
f 括号部分删除。
g括号部分删除。
h 从“尽管”到“历史意义”这段字句删除。
i“建立在……基础之上的”这段字句删除。
j括号部分删除。
k从“人的本质的基础”到“改良主义”这段字句删除。
l 这些句子被删除。
m “思考尚未被思考的东西”。
n “并被资产阶级……所代表”整个删除。
o 此句删除。
p “因为……是什么”整句删除。
q “在这种……烙印”整句删除。
r “有一个本地的例子……无政府工团主义”整句删除。
s 此句删除。
t “工会的首创……旧有观念”整句删除。
u “从而通过党的意识形态确保着它的‘路线’的统治地位”。
v . 普朗查斯后来做出了这样的评论:“就这个方面而言,我认为阿尔都塞出色地总结了有关(大写)国家的第三国际传统立场。我曾多次指出过,该立场涉及这样一种工具主义的观念:(大写)国家作为工具或[机器]……可以任由统治阶级操纵。权力是一种可量化的实体,体现在假设为对象化的这种(大写)国家之中。它被人以从机械隐喻到拓扑隐喻的方式做了这样的描述:国家除了官僚机构的臃肿无能等方面之外,构成了毫无缝隙的铁板一块。作为阶级矛盾的国家内在矛盾绝不可能是国家的坚硬内核[……]工具主义国家观,同时也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国家观:人民群众既被包含于其中——被整个城堡中蔓延开来的资产阶级瘟疫‘包围’进而被污染,但还保持着纯洁[……],后来便被完全被移出城堡的大墙之外[……]。与这种本质主义观念不同,我而认为国家应该被理解成为一种关系,更确切地说,是阶级与阶级之间、阶级各阶层之间权力斗争的物质凝缩。权力本身并不是一种可量化的本质,而是一种关系。(大写)国家正是由阶级矛盾构成的,这些具有具体形式的矛盾乃是国家的内在矛盾[……]。我们不仅要从内部与外部的角度,而且更要从战略地形和过程的角度在这里进行思考:群众斗争,就其政治方面来说,仍旧处在(大写)国家的场地之内。党不可能完全将自己置身于(大写)国家之外。夺取(大写)国家权力因而是一项长期的策略,其最基本的方针就是对甚至处在(大写)国家场地之内的力量关系进行调整,并利用(大写)国家的内在矛盾 [……]对这样的党来说,置身于(大写)的国家的场地之中,恰恰相反并不意味着(那样做的确十分危险)与国家的物质机器相结合并在管理模式上完全照搬它,或完全认同于它。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组织的独立性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而不在这种组织与(大写)国家的分离当中”( “党的危机”(La crise des partis),载于 “辩证干预”丛书《方位标》(Repères, Paris, Maspero, coll. «Dialectiques-Interventions», 1980))第172到174页。艾蒂安·巴利巴尔也将发展出一种与之相当类似的观点,恰恰就在“独立于国家”的党这个问题地上,他与阿尔都塞拉开了政治距离。
w 括号部分删除。
x “人民和‘异议者’或反对者”。
y 几年之后,博比奥将反驳阿尔都塞:“这难道不是一个几乎一般性的断言吗?根据阿尔都塞的说法,问题不在于废除所有的游戏规则。好极了:但怎么得知哪些要被废除,哪些不能废除呢?在与民主制度一样细致和连贯的制度中——这种制度从程序来看是细致而连贯的,而正是该制度赋予程序以生命,二百年来这种制度与其程序相互依赖——,有绝对的把握将可以保留的规则和应该废黜的规则区别开来,这真的是可能的吗?我们在普选中有所保留反倒是没有意见自由吗?意见自由反倒不是政党多元吗?政党多元反倒不是民权的法律保障吗?说到底,对不是所有的游戏规则都将被废除的强调,乃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恰恰对与游戏规则问题同样核心的问题避而不谈;做如此断言只能说明,断言者对这类问题如何解决是一无所知的”,“民主的限制(I vincoli della democrazia)”,载于《民主的未来:为游戏规则辩护》(Il futuro della democrazia. Una difesa della regole del giocco, Turin Einaudi 1984)第56—57页。
z “除了……悲剧”整句删除。
aa 词句删除。
bb 接下来的三个段落删除。
cc “因为……”诸句删除。
dd 后有括号补充说明:“实际的或一般的”。
ee “而未……物质性层面”一句删除。
ff “对政治进行社会化”;“‘特殊’政治的‘扩散性’”;“分子扩散状态的政治”;“(大写)国家扩散”
gg “我很难接受总体形式、领导权、建国的说法:在这里……”
hh 博比奥后来撰写了一篇长文评论阿尔都塞的这篇文本以及它所引发的争论。此文的观点可以总结如下:围绕“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是否就是所谓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那些制度的严重缺陷的理由或理由之一?”这一问题而展开的讨论,很难进一步推进。关于此,可以做出两条说明:1)首先涉及“马克思主义者们对待(大写)国家问题时进入了狭隘的文化视野”,他们完全没有参考韦伯、帕森斯或施米特等作家,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症状。然而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有限的”理论的话,这也意味着完全有可能确定它与其外部之间的差距——而进行之中的讨论却完全没有做到这一点。2)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在这场讨论中各说各话。从传统来看,政治理论以最高权力的组织——使统治权的行使成为可能的各类机制,以及被统治者对它们的控制——为对象,然而每个理论家都各自以对立两极中的一极为自己的侧重点。西方国家的特点在于,以渐进的方式逐步强调个人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它们构成了民主的三个相关的基本要素。然而,马克思主义者们似乎对这三种权力和他们界定的(大写)国家形式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是满足于使用“资产阶级”或“资本家”之类的词语,“但用什么来替代它们呢?未解之谜。”在这场讨论之中,“吸引参与者兴趣的主题并非是权力组织的模式,而是夺取权力的方式”。但关键的是,知道在“游戏规则”当中,哪些是要革除的,哪些是要创造的或革命化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他们也不可能有关于(大写)国家的理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将(游戏各方都遵守的)“游戏规则”与(各方各自不同的)“进行游戏的规则”或换言之“政治策略”区别开来。任何国家理论从根本上说谈的都是前者,而马克思主义者最感兴趣的则是后者。博比奥通过说明自己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来总结了自己的论点,他指出他自己既非马克思主义者也非反马克思主义者。简而言之,马克思是人们必须面对的一个经典。实际上,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危机了,不如说是那些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普遍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陷入了危机。然而,即便它是一种“有限的”理论,也没有理由断言它陷入了危机,正如同样没有什么理由断言面对批评的韦伯式资本主义起源理论一样陷入了危机一样。“马克思的工作,尽管其中存在错误和空白,仍旧并且必将仍旧取得成就,虽然在太多情况下危机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将变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与阿尔都塞商榷。坚持要发现一种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危机(Discutendo con Althusser. La crisi è dei marxisti, che si ostinano a cercare una teoria marxista dello stato)”,载《宣言报》,1978年5月30日)。
长按识别二维码
关注“公众号”
点
这里“阅读原文”,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