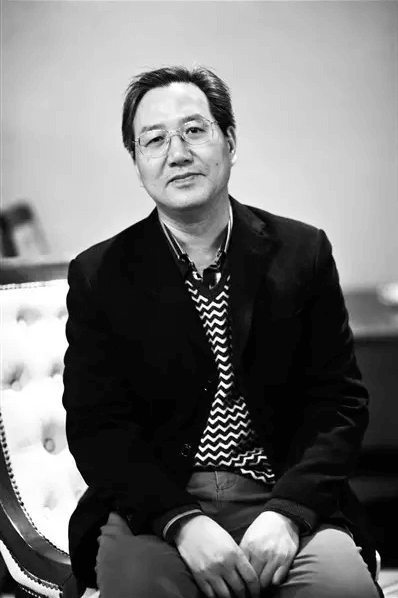原编者按:国民党政权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党治政权。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政治形态在漫长的王朝帝制崩溃后,开始向一种新的党国体制转型。中国从此步入党治时代。经王奇生老师授权,我们选用下面这篇文章,喜欢或关注国共历史的读者朋友尤可一读。
弱势独裁政党的历史命运
王奇生
国民党仿照俄共实行一党专政,而在实际运作中,其组织散漫性,又像西方议会政党。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国民党并非不想独裁,而是独裁之心有余,独裁之力不足。
(一)
1927年3月6日晚8时,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在上海环龙路26号与中共总书记陈独秀闲谈。在座的还有钮永建、杨铨、罗亦农等人。
吴问陈:“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需要若干年?”
“20年!”陈毫不迟疑地回答。
吴作骇极之状。罗在一旁似怪陈过于直率。
合座默然。
吴即乱以闲语曰:“由此,国民党生命止剩19年了。前时总理答越飞,国民党国民革命完成,应需三十年。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得[代]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应当通盘商量才好!”[1]
这一场景对话,出自吴稚晖于“四一二政变”前夕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提交的弹劾共产党文。当年陈独秀“二十年”之说,也许只是国共朋友之间私下闲聊之语,吴稚晖却以之为清党反共的借口,显然有借题发挥之嫌。而陈之闲语在22年之后竟成现实,恐是当年吴稚晖和陈独秀均未曾预料的。
不过,就国共在北伐时期的组织实力而论,两党若仅以组织对组织,以运动对运动,仅“文斗”而非“武斗”的话,共产党取代国民党的时间可能还要提前许多。1924年改组以后的国民党,虽然在组织形式上师法苏俄共产党,实际只学到半套表面功夫。中共以一个数百人的小党、幼党,加入到一个几十万人的大党、老党之中,仅用两三年时间,即反客为主,“容共”几乎逆转为“容国”。倘非蒋介石断然以武力清共,国共之间或许早已和平演变。
1927年后,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师法苏俄实行一党专政。但此时的国民党实际上根本不具备专政的社会条件和自身实力。中共执掌全国政权时,拥有600多万党员,其中脱产干部331万人(1952年),到1958年,党员人数增至1300余万,脱产干部增至792万。以如此众多之党员干部,共产党尚感不能满足其新政权组织建设的需要。[2]而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之初(1929年),普通党员仅27万余人,到1937年,亦不过52万余人。1929年,南京政府仅控制了约8%的国土和20%的人口;抗战前夕,它所能控制的地区和人口分别增至25%和66%。[3]但这种控制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由于党力不足,南京政府一方面只能将政治触角囿限于上层和城市,县以下农村基层社会任由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打着其旗号胡作非为;另一方面,大量吸纳北洋旧官僚进入其各级政权系统,使北洋官场旧习得以在新政权中延续下来。
抗战时期,国民党的组织规模得到空前扩张,但大多数党员只是挂名党籍。党不能在农村、工厂、矿山、铁路以及其他部门中建立深厚的组织基础,也不能在民间团体和社会组织中建立健全的政治领导。40年代的国民党几乎丧失了作为一个政党的基本组织机能和活力。1941年,“阎锡山对其左右明言,以后国民党、共产党与汪伪三方面之成败,共党则为六分之三,汪逆则为六分之二,国民党则仅有六分之一之希望。”[4]
国民党始终未能建立一个具有严密渗透性和强大内聚力的政党组织体系。国民党政权的支撑力量不是党员和党机器,而是军人和武力。在党、政、军三者之中,党的力量最为脆弱。无论战时抗日,还是战后“剿共”,最先瓦解的往往是党部,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军队;收复某一个地方,最先到达的首先是军队,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党部。而共产党则相反,党的力量往往成为军政的前锋,攻占某一地区,最先打入的首先是党组织,然后军政力量跟进;从某一地区撤退时,即使军政力量退出后,党的组织仍然留下来继续战斗。在共产党那里,党充分发挥了政治核心的作用;而在国民党那里,党完全沦为军政的附庸。
国民党执政以后没有触动既存的社会结构。国民党不是派遣和选拔政治上合格的党员进入各级政治和社会机构中去改造和建立新的立足点,也不是培养党员成为社会各界的楷模,以赢得民众的信仰和拥护,而是不加甄别地网罗旧的社会权势力量加入国民党。那些人戴上国民党党徽,只是为了继续保住其既有权势资源和维护旧的社会政治秩序。
在社会整合方面,国民党的组织和影响也未能深入到社会底层和辐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三四十年代的大量资料显示,国民党在广大农村基层社会的影响甚至不如乡村教会组织和秘密社会团体。以四川为例,该省哥老会的势力和影响远远超过了国民党。党和政府的许多政策措施只有在取得当地哥老会首领的首肯后才能推行。
蒋介石秘密特务组织活动之猖獗,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人们对国民党法西斯强权政治的印象。国民党党机器的软弱无能,与其特务活动的猖狂肆虐,形成强烈的反差。美国学者易劳逸认为:“国民党政权在本质上是矛盾的:它时而专横暴虐,时而又虚弱妥协。在独裁的外观之下,其权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对一支占优势的军事力量的控制。”[5]事实上,国民党的专横暴虐,与其软弱无能是相因相成的。蒋介石依赖特务实行控制,与其说是其铁腕权力的表现,不如说是他在党机器软弱无能,无法控制政治和社会局面之下的无奈之举。30年代的力行社和40年代的三青团,均是蒋介石痛感党机器软弱无能而不得不另起炉灶的结果。
(二)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陷入党魁换代危机的权力纠葛中。清党以后,党内意识形态认同危机又相继引发。党统之争、路线之争与地方实力派的地盘之争交相杂糅。在这一过程中,蒋介石以军权坐大,最终以军权控扼党权。蒋介石认为,任何社会,任何时代,军人都是社会的主导群体;人类社会最合理、最严密、最有效的组织,莫过于军事统制。与军事统制相比,政党组织的社会动员功能显得软弱无力和无足轻重。蒋介石对军权和军治的过分迷恋,分散甚至取代了他对党机器组织建设的关注和考虑。在蒋的一生中,他最为倚赖的是军队,而不是党。
在蒋介石重军轻党思想的主导下,军权日趋膨胀,党权日趋低落。从中央至地方,军权凌驾于党政之上,党治徒有其表。国民党党治体制的法理序列是党→政→军,而实际序列却是军→政→党;名义上是以党治政,以党治军,实际上是以军统政,以军控党。
苏俄党治自上而下贯彻到底,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党权真正高于一切,党权对政权处于绝对领导地位。而国民党没有仿行。在地方层级,国民党中央不允许地方党部直接干预地方行政。地方政权的重心在政不在党。党部被置于次要和无足轻重的地位。党部没有人事组织权,无法通过管理从政党员去制约和监督政府,党组织对党员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党权在地方层级因无所寄托而日趋弱化。
自清末废科举后,旧的官僚选拔机制不复存在,而新的政治录用制度一直未能建立。作为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本可通过严格的党员吸纳机制,将切实认奉党的意识形态的党员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国家政权的官僚队伍,建立一套新的政治录用体制。但国民党的人事制度很不健全。国民党中央虽有“用人先用党员,裁人先裁非党员”的规定,但在实际运作中并没有切实执行。党员在政治地位和晋升机会上,比非党员并无明显的或潜在的优越性。党员既无政治内幕的知悉权,更无政治决策的参与权。
另一方面,党员对派系的忠诚大大超过了对党的忠诚。党机器由北伐时期指导全国政治军事的核心权力组织逐渐蜕变为一个特定的政治派别所独掌和垄断的权力工具。蒋介石长期将党务组织大权畀予二陈兄弟,遂使以二陈为首的CC系势力极度膨胀,并导致国民党党务资源由“公领域”向派系的“私领域”大量流失。一国之党蜕变为一派之党。在“党务派系化”的同时,另一些派系发展成为一种富有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准政党组织。战前力行社和战时三青团即是“派系党化”的典型。
(三)
1948年11月20日,蒋介石批准陈果夫赴台养病,党内职务另择人代理。陈果夫在当日日记中写道:“党的宣传为民主自由,党的训练为军事化,党的组织为学苏联,内部是中国的。如此东拼西凑,不成一套,如何是好?”[6]陈果夫的这一番牢骚话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国民党体制所存在的缺陷。
从1924年起,国民党师法俄共(布)的组织形式,将党建在国上,实行以党治国,一党专政。但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理念中的政治蓝图又是基于西方民主体制而设计的。这样一来,国民党实际上是借鉴两个不能同时并立的政治架构,拼装了一台不伦不类的政治机器,一方面依照西方分权学说,成立了五院,另一方面又依照苏俄党治学说,设立了集权的中执会、中政会。在欧美民主政治国家,有立法、司法、行政等分权的机关,没有党治的那些委员会;而在苏俄那样的党治国家里,有集权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委员会,却无分权的独立机关。而国民党则兼收并蓄。
事实证明,这种兼收并蓄,弊漏百出。一方面,国民党对政权的独占和垄断,意味着孙中山所设计的民主宪政蓝图成为泡影;另一方面,三民主义体系中的民主宪政目标,又使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也时常成为体制外势力用来批判和攻击其党治的有力武器。
国民党仿照俄共实行一党专政,而在实际运作中,其组织散漫性,又像西方议会政党。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国民党并非不想独裁,而是独裁之心有余,独裁之力不足。
国共分家后,国民党漠视当时中国实际存在的阶级对立和冲突,声称代表“全民”利益,而这样一种“全民”利益实际上并不存在。国民党企图把本身的基础建立在彼此利益相互冲突的各阶级联盟之上,其结果却是两不讨好。“全民”中没有哪一个阶级,真正认同或感觉到国民党确实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国民党自然也没有一个真正属于它的社会阶级基础。
1947年9月,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及党团联席会议在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决议将三青团并入国民党,所有党员、团员一律重新登记为党员。合并前夕,国民党中央公布的党员人数:普通党员377万,军人党员485万,合计为862万。[7]三青团团员154万。[8]党、团合并后,国民党党员总数当超过1千万。
但是,截至1948年11月,党员、团员重新登记为党员者仅132万。[9]也就是说,在党、团合并过程中,将近九成的党、团员实际已脱离了国民党。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自1947年起,停发县级党务经费,让县以下基层干部自谋生路。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县党部仅留下一两人做做例行的“总理纪念周”,有的县党部干脆人去楼空,空悬一块白底黑字的招牌,任其在风雨之中摇曳。
此情此景,寓意着国民党早在军事大溃败之前,实际上已“先天下之亡而亡”了。
(选自《党员、党权与党争: 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华文出版社,2010年10月)
王奇生,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武汉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先后任职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等。
[1]《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敬恒呈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文》,见1927年4月16日《广州民国日报》。另见《吴敬恒致中央监察委员会请查办共产党函》(1927年4月2日),载蒋永敬编《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版,第362-363页。
[2]詹姆斯.R.汤森等:《中国政治》,顾速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页。
[3]易劳逸:《流产的革命》,第331页。
[4]蒋介石1941年6月26日日记。
[5]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二),第149、152页。
[6]徐咏平:《陈果夫传》,第952页。
[7]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下),第588页。
[8]王良卿:《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研究》,第116页。
[9]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下),第544页。